观点 SLA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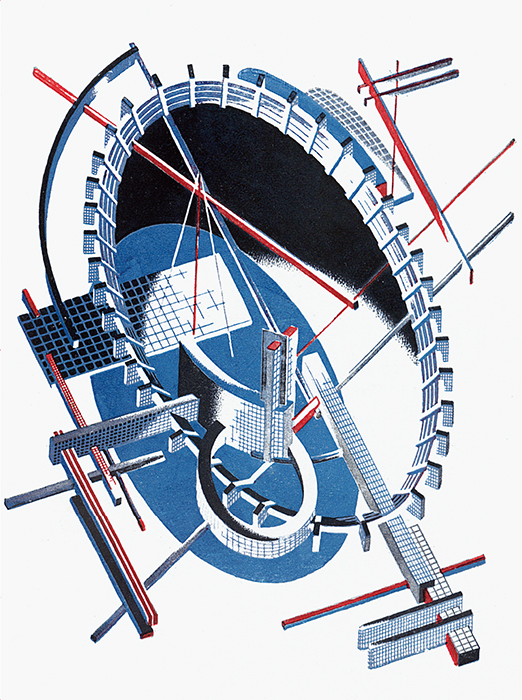
如果你们以为我们能从大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那你们就不是革命者,而是改良主义者或空想主义者。
——列宁,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1921年12月20日
在《银翼杀手2049》中,已将视觉系统升级的企业主华莱士说道,“任何文明都是建立在一支可支配的劳动力大军之上”,复制人是未来,可其制造周期有限,由此可育复制人(可再生产)就成了最理想的奴隶。与此片的好莱坞趣味所极力渲染的“生殖人性”不同,电影在这一刻透过华莱士吐露出“银翼”系列片的赛博朋克线索——现代统治与可控肉体之间的关系,对这一关系,或许福柯(规训与惩戒,1975)的概括更为直白:只有在肉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这种知识和这种驾驭可以称为肉体的政治技术学。
驯服与否的斗争构成了主奴辩证的历史寓言,然而“银翼”系列的人性母题压抑了主奴关系的有效表达。当奴隶在生产过程中不断习得经验、知识、协作,理解了人与人的生产关系,明白了劳动者的联合如何改变世界,这时候复制人还会仅仅是为了获得做人的权力,拥有出生、成长与死亡的体验而反抗吗?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正不断生产出新的价值和新的自我,不会意识到主人所要实现的真理已经在奴隶一边了吗?
于是,当人被从土地中拔除、被迫流动、一无所有、成为可供买卖的自由劳动力,现代资本主义在食取这巨大剩余价值的同时,也时刻面临着规训与管控危机。对于劳动者而言,这只是革命的辩证可能,并不解答革命如何发生;相反,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家里,工人贵族可与资本达成和解,通过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剥削可以转向外部,转往知识上“非人”的领地,这正如华莱士生产的复制人劳作于地外行星。在现代资本扩张的大部分时间里,历史都是福柯式的展开,呈现为关于人口和领土的永恒治理与斗争,而“革命”并不一定会按时到来——按照齐泽克的说法,革命只能在历史的空隙中,“逆流”发生。在整个20世纪里,所有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吸纳农民和民族解放的“暴力潜能”中创生出来的。
于是,革命并不始于先进的生产力,而更可能来自资本和帝国主义最外围的绝望反抗,但革命的目的显然不只是“做人的权力”,而是不惜一切代价对历史的惰性进行强力干预的乌托邦意志。在此,齐泽克认为列宁在如何夺权上是个实用主义者,而在用权力做什么上又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对我来说,这种在反抗与夺权的辩证统一中展开的行动,才叫做革命。
十月革命的第四周年,正在推行新经济政策的列宁在《真理报》上写道:“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导到共产主义。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另一方面,也正是在以意志扭转历史的过渡时期,各种新社会的技术与文化革命才得以展开。高尔基认为艺术可以成为激发政治行动的手段,动员个体摆脱狭隘的个人利益为更大公共事业服务。博格丹诺夫(Alexander Bogdanov)走得更远,他认为劳动者不应该是等待被宣传和规训的肉身,而是文化的生产者。工人一旦获得了体系性的支持,他们将不再是资本主义机器上的齿轮,而将成为新社会的集体经验和知识的来源。在人民教育委员会的资助下,“Proletkult”(由“无产阶级”与“文化”两个词组成)运动随着苏联的建立扩散到主要的工业城市,工艺技术、绘画和电影工作坊、戏剧、建筑和摄影课程直接开在车间里——我们后来所熟知的一些现代主义先锋艺术流派,如未来主义和构成主义皆与之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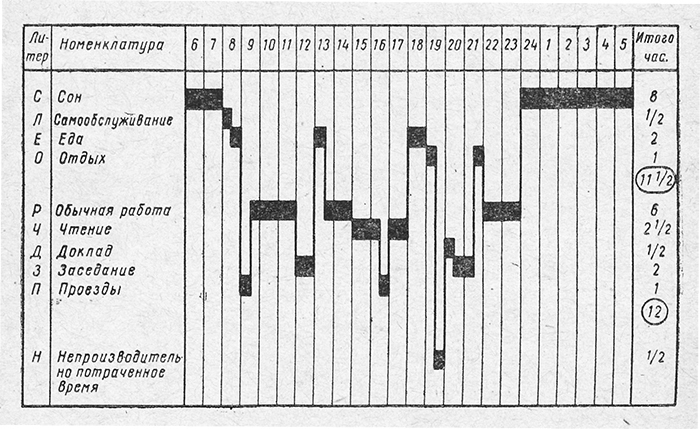
革命给20世纪带来的远远不止现代主义。1925年凯恩斯前往苏联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在同年出版的游记《俄国掠影》中,他虽坦言自己并非社会主义者,不过于次年1926年发表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并由此开启与哈耶克长达半个世纪的论战。大萧条后,罗斯福的“新政”不单借鉴了苏联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还仿效Proletkult实行了面向工人和艺术家的全国性公共艺术项目——公共艺术计划(PWAP)、联邦艺术计划(FAP)、联邦作家计划(FWP)、联邦戏剧计划(FTP)等。大量资助公共艺术的基金会也在这一时期成立。美国人恐惧自己的国家赤化,但并不忌讳向对手学习。
作为列宁的党内同志和对手,博格丹诺夫的影响也许更为深远,他在政治经济和文教问题上的系统论思维集中呈现在1913年出版的《组织构造学:一种通用的组织科学》(Tektology: A Universal Organizational Science)中。Tektology认为,社会同生物界一样是一个开放系统,一切社会科学的根本都是“组织”问题,是处理“自发性”和“系统均衡”的控制命题,正如Proletkult的基础架构可以生长出无产阶级自组织的文化。这种自下而上的哲学在欧洲那些恐惧苏联集权的政党中找到了同路人。1919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执政后,在红色维也纳(Red Vienna)发起了一场社会主义的文化实验——知识的社会化,公共讲座、艺术、建筑和出版成为提升心灵的基础条件。维也纳圈(Vienna Circle)的关键人物奥图·纽拉特(Otto Neurath)认为全面的知识生产必须基于易于学习和传播的基础设施,他设想了一套叫做ISOTYPE(International System of Typographic Picture Education)的图像语言,使得统计学和现代主义审美相结合,“将社会和经济状况呈现给大众,提升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打碎资本主义对物的膜拜”。作为平面设计和数据可视化的先驱,纽拉特的创造完全是为了探索更加民主和合理的中央计划模式。红色维也纳自治市虽然在1934年终结,奥国马克思主义者(Austromarxists)的实践却在教育、医疗和公共住宅等方面启发了北欧的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共党。战争时期,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已经开始资助纽拉特的工作。随着战后奥地利圈知识分子跨越大西洋,他们的数学和统计技术奠定了美国战后的量化社会科学,不过不再是为了实验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主义,而是服务于冷战中的军事与社会控制。
博格丹诺夫的德文译本影响了斯拉夫裔的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后者在二战期间使用相似的语言提出了控制论(cybernetics)——生物、机器与社会的通用反馈原理。沃伦·韦弗在战后代表美国政府和军方利益整合了这一领域,开启了关于社会控制的信息科学。维纳过早地洞察到冷战的战略目标和他的初衷背道而驰,于是与军方渐行渐远,转而在自动化与人力替代的问题上发出警告。
1949年,维纳写道:“自动化时代的美景,是机械奴隶将代替人类工作,而人成为自由的、躺在吊床里的思想家。但这可能并不是未来实际的样子。机器劳动虽然与奴隶劳动不同,并不包含直接的人身虐待和剥削;可是,任何劳动,只要接受了与奴隶劳动竞争的条件,也就是接受了奴隶劳动的条件,它在本质上就是奴隶劳动。”维纳认为,问题的关键在“竞争”,如果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掘地工不得不与掘土机竞争,直到工资低至不能活命,那控制论革命的后果很可能使得具有中等能力的脑力劳动者失去任何可以出卖的技能。科学家有责任把这个局势告诉关心劳动条件和前途的人——劳工联合会。维纳认为这将是赛博时代“我们必须面对的最大挑战”。然而,维纳与劳联的接触并不顺利,“劳工联合会和劳工运动掌握在一群有很大局限性的人手中,他们在工资与工作条件的专门问题争取方面有极好的训练,但完全不愿意参与更大的政治、技术、社会和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正在牵涉到劳工本身的存续。”

有趣的是,维纳的问题意识在女性主义当代艺术那里得到了迅速回应,艺术家卡若莉·史尼曼(Carolee Schneemann)、爱丽丝·艾考克(Alice Aycock)、阿格内丝·丹尼斯( Agnes Denes)、玛莎·罗斯勒(Martha Rosler)等反对控制论的武器应用,设想了一种反冷战的女性主义乌托邦。在其另类未来中,“边界”被“渗透膜”取代,“机器”被“生命体”取代,父权制的封闭系统被去中心化的开放系统取代,信息技术将摆脱剥削和压抑的属性,变为身份解放的中介。
冷战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从北美回流到后斯大林东方阵营的控制论成为了替代马克思主义官方意识形态的另类选择。1960年6月,维纳受苏联官方邀请访问了莫斯科,成为在冷战中实现跨阵营交流的少数几个科学家之一。苏联媒体将他塑造成预言了一门社会主义科学的外国先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一切学科被要求在控制论的统摄下重组,雄心勃勃的全国互联网工程(OGAS)甚至要早于Internet。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小说家斯坦尼斯拉·莱姆(Stanislaw Lem)作为控制论未来主义(cybernetics futurologist)的先行者,在《技术总论》(Summa Technologiae)中首次触及了人体的赛博格化问题,如果无线电技术可以像义肢一样替代语言器官,“那嘴将消亡,由此星际交往就成为可能”,这后来成了《索拉里斯》(Solaris)中那个不可捉摸的非人类生命体。莱姆的后人类预言,连同苏联艺术家小组Dvizhenie的赛博剧场(Cybertheatre)、波兰画家耶日·罗梭洛维奇(Jerzy Rosolowicz)的“Neutrdrom”系列等作品,动员了1970到1980年代的东欧反共异见分子。
赛博革命由红色转向蓝色的同时,也侵蚀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地基。如果思维只是系统的一部分,我们的肉体不再是个体自足的边界,行动来自于反馈而不是内省——自主、充分的“自我”将变成一种错觉。在战后法国,关于控制论的公共讨论承接了知识分子对于笛卡尔哲学的固有兴趣,启发了理论界的后结构主义转向:还在军中服役的青年精神分析师雅克·拉康可能是早期控制论成员;德勒兹在掌握了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的信息理论后,放弃了对意义的分析;瓜塔里、福柯和其他理论家已经可以对编码、解码、信息和通讯等术语进行熟练的使用。在美国情报部门和基金会的支持下,新哲学和思想家的崛起帮助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最后的合法性。
在二十世纪的尾声,历史又被带回到了福柯式的节奏里——用福柯的考古学语言来说,“人”作为一项晚近发明的同时,也正在走向其终结。或者换用马克思的辩证概括:“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而在这短暂的属于生命的“理智时刻”,革命是“劳动的人”的集体意志在二十世纪生成的独特构造,是一种临界状态。天体物理学知识告诉我们,壮丽的超新星爆发源自恒星内核的引力塌缩。回溯革命与技术政治在20世纪的历史,也正是革命的坍缩抛射出这些构成革命根本性难题的碎片。不管是理论的还是技术的,这些碎片异常激烈、炫目,每一块都播放着革命亦或告别革命的故事,渴望着应许之地——从人工智能到平台共产主义、从先锋艺术到大数据治理、从绝望的穆斯林弃民到流水线上的中国工人……革命的碎片四散开去忘记了自己的来路,这是后革命时代的典型症状。
在1982年《银翼杀手》的末尾,只有7年生命的复制人罗伊在屋顶迎接自己的死亡:
我所见过的事物,你们人类绝对无法置信
我目睹了战船在猎户星座的端沿起火燃烧
我看着C射线在唐怀瑟之门附近的黑暗中闪烁
所有这些时刻 终将流逝在时光中
一如眼泪
消失在雨中
反抗的欲望抛落在革命的余烬里,一如眼泪消失在雨中。

文/ 王洪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