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亲爱的乙烯,
那天下午听你说了两个Borges的短篇。在你说了第一个侦探的故事之后,我就想,啊,第二个故事应该就是两个国王与两个迷宫吧。然后你说了。一边很愉快的时候,突然间整个听讲的空间有了不均匀的陷落:初次听这些故事的人和第一百次复习这些故事的人被震开来,从此分属于不同图层。
且让我们称之为“阿尔戈是尤里西斯的狗”效应。
这个效应只有在讲者讲的内容又深刻又有意思的时候才会出现,没意思的讲者只会让我火大。我在每次脑与脑的对质——不管我面对的是人或是作品——发生前都会全心全意期待“阿尔戈是尤里西斯的狗”效应,但当效应达成使我法喜充满之时却又会在下一秒世界级悲伤。当一个生产者在拆开自己的脑展示给人看的时候,有多少人是看着同盟的战略并对应想着自己的战略,又有多少人只是纯欣赏一个“天才”在高速运转后从耳朵散发滚脑浆的味道?而我们都知道,造物者之懒惰就是在于它尽是造一堆能分辨出“谁不是天才”的人,却吝啬于做一个真的天才来。天才可能不是什么准确的字啦,我的意思是,在这种人身上,时间和经验都作用得非常慷慨,同一单位input的密度和其他人完全没得比,因此在output的时候,他们处理及发话对象每每起手就是一整个叫世界的幅员,一整个叫人类的物种,而这种人对其他人——同代人也好、差了几个世纪也好——的影响就是,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活生生”:觉得自己有可能,觉得自己有可能“有可能”。
永恒之城的人、天才、朋友——我一直胡乱交错使用这些明明意思迥异的字,或许在无聊的课程或访谈中这会是“谁是你的创作参照”的问题,但这种提问方式每每让我觉得怪:一是光听就非常功利,二是这哪有可能是像点菜一样的思考方式呢?这不是形式或内容上口味合不合的问题,而是在路狭且长的小径上,有人曾经因为(在我们各自的定义下认为)活得很好而让我们也觉得“活着”这个丑怪的动作是值得一试的。在这样的前提下,可能遍寻整个活在相同时间轴的同辈都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因此这问题的答案不是一串人名,而是造一座私人的永恒之城:我来决定谁不仅值得活过,且值得永生,被我允许进驻的人经过“阿尔戈是尤里西斯的狗”效应的重重检验,成为我定义的天才,而我称他们为朋友。我需要一座这样的城以让作为创作者的我活着。
是说我也不清楚到底这对写是不是真的围绕着什么命题,老实说我就是为了对写而对写,因为我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长聊中,当你说“关心历史与关心历史书写是差很多的”之时,我超级激动,那天回家之后我在我的(不是每天写的)日记上最后一段是写这样“我的意思是,不管我到底认不认识这位作家,但那瞬间我有一个想像的朋友,一个萝卜一个坑长得就是我需要的样子,让我深深感激。”所以,基于这个不知道准不准的一眼一瞬间,我想你是我最适合讨论朋友问题(=创作者之孤独问题(=创作者之生存问题))的人了。
(去年十一月我人在oaxaca,朋友带我去看在地的亡灵节是什么样子,总之在跟着鬼们绕民宅很远之后,最后回到一个大广场,大广场挤满了人,肩膀贴肩膀到肉变形的程度,有乐队正在无限重复一段传统的旋律,大家在尖叫跟勉强舞蹈。朋友说,他们称这种景象叫地狱,“你准备好要去地狱了吗?”他笑着说,其实我超级怕人,但在那个瞬间我说:好啊(管他去死)。)
期待你的回信。
亲爱的纹瑄
(以下每一段互相都没什么关系)
似乎是用自由通信来暖机
但或许,比起有题目的对写会很快跳入专业地就着某个什么说起来
反而是关于友谊的自由,要困难得多。
毕竟,如同你一定也一再经历的
和谁有过怎样美丽或至少值得的交锋
可当合作完毕,这个人就从生命中(暂时?)消失了
这两场活动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太少太少机会可以真的对人说那些我在意的事。但同时我也感到非常沮丧,因为觉得表现得很差。
也许是平常的演讲毕竟是关于主办方已订的题目,结构已经预设在那里,你只要一直填进洞就好。而写作时,我本来就是会一直一直调整,像科学家那样在意一切的逻辑,毕竟即使是一个介词或标点都会写定论述的破绽。
当然或尤其还有诗,诗的气氛该是滴水不漏的。
所以在创造话语环境时,变得那么斑驳而难以忍受。但这种俗气的创作洁癖也没什么好说的。
读你的信真是觉得,仿佛这次准备Borges这个展演,就是为了能得到这样一封信似的。
没意思的讲者与其让我火大,不如说让我困惑:
我无法不想:
“是我搞错了什么吗?(为什么他要这么琐碎、这么无趣、这么通篇都是现成讯息、这么全部都是人家讲过的话)”
但多数时候就是如此。你用力去听、去读一个东西,然后怎么样都找不出其中有作者纯粹思考后的发现。像是宇宙与未来都是现成的了,大家只要一直复制贴上就好了。这让我觉得不耐烦。也觉得很孤单。
那天在居酒屋和你聊完天回家,我在想我遇到了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人。
就算只是在某个方面,却是于我而言最重要的面向。
我曾经在许多电影和小说里自以为看到了某个东西,它们一直频繁地出现,以致于我觉得这世界有发展这件事的空间。但慢慢地我觉得就算真成立这方面的题目,它也并不被重视,人们并不期望要再多走太远。
我曾认为那就是理论的未来。但后来我开始怀疑它将会一直这么边缘。
由于这件事大概就是我的命运了,所以我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但我不打算用传教的方式去提倡、游说、催眠,我只想坚持这件事然后把它变成像是同时是游戏与挑衅,由此对抗那些我觉得老到不能再老的理论与艺术观。
我喜欢你说的
“造一座私人的永恒之城:我来决定谁不仅值得活过,且值得永生,被我允许进驻的人经过‘阿尔戈是尤里西斯的狗’效应的重重检验,成为我定义的天才,而我称他们为朋友。我需要一座这样的城以让作为创作者的我活着。”
不用急着回信。
yours,
e
Dear
发现信上没有一个补充说明,以致于看起来有点没头没脑的。我想我们可以先乱说一点什么(因为相较于你的篇章已经完全可以直接回应对写题目,我却还在很周边地乱晃)。
然后感觉双方的韵律与倾向,再订出一个大纲。
其实这个题目可以谈很多概念,但我也希望如果可能的话说不定我们可以为其中注入一种真正的亲密感。就也有了文学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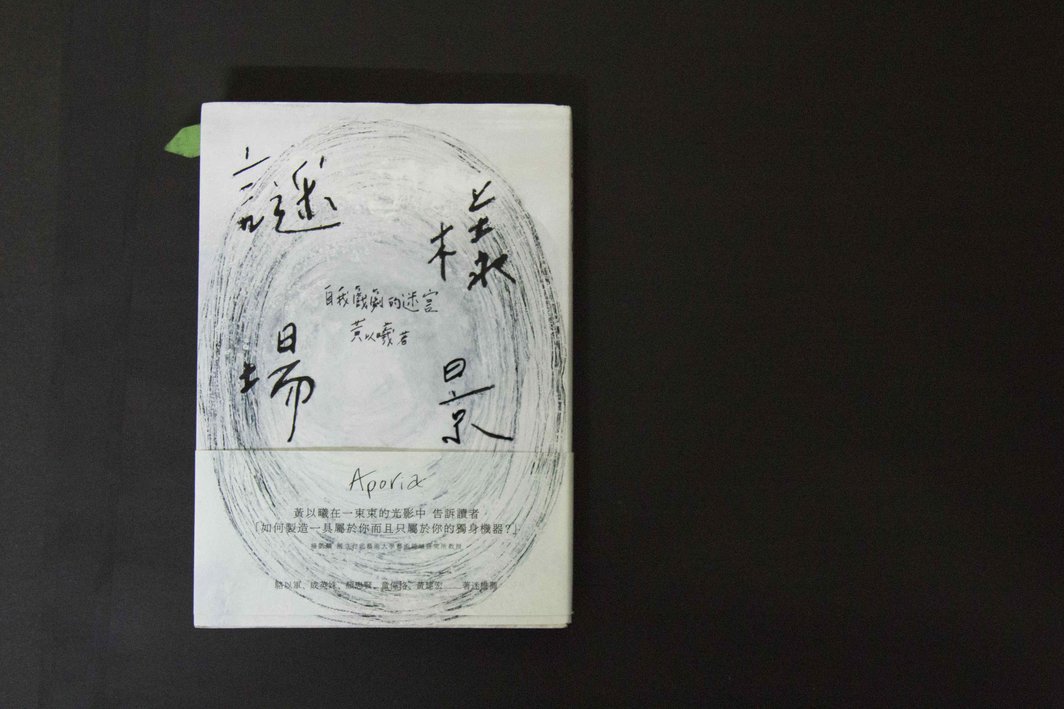
亲爱的乙烯,
就像你说的那样,有太多美丽的交锋是好东西却也是一次性的东西,某个节骨眼就停了,让人遗憾。如果是工作上的合作那就是普通遗憾,但如果是基于自由意志开启的对话那就是非常遗憾。在后者的情况中,当某种“求偶”的态势出现,通常就也预告了之后的无疾而终。不晓得你会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也就是原本好像在针对一个真正的问题讨论,突然间变成了费洛蒙大赛,即使A不是故意的,但他的专注与张嘴就掉出来的星星月亮太阳,在B的那边却像是勾引,他必须也以星星月亮太阳的方式回应A——在此,真正的问题退位,变成两只鸟在跳舞。所以在看到你说“注入一种真正的亲密感”并因此“有文学性”,在附议的同时也在想,说不定这是个比看起来难得多的挑战,因为这变成是要在欣赏另一个脑的时候,维持住自己的状态,才能一直专注在真正的问题本身,而不只是在修辞上修辞。
后来想了几天,发现我之所以这么在意这件事,可能是因为我之前有遭遇类似的情况:在当场惊觉我和观众之间的“有互动”都是假动作,都是一场误会。好比,你的场子来的人很多,他们应该也觉得很有收获,好看又好听,从活动纪录来看是个成功的public program——但观众仍然是以一般听讲座的受教、欣赏心态来,如此舒服而这并不是你想要的;又好比,对我来说我念兹在兹的有两件事(1)我不在作品中使用到任何独一无二的正本强化人证物证本身的价值(2)我不是在处理历史事实(这也是我最重要的关切但像你一样没能有机会谈),但九成的观众(不管是专业与否)都会“阿张纹瑄在处理历史处理得很认真。(盖章结案)”。
对我来说lecture performance和lecture二者最大的差异就是,藉由每分每秒让观众意识到距离,他会因此感受到“演”、感受到“假”、感受到“不舒服”,因为被表演的不是角色,而是“某人正在教”的这个阶层化事实,只有在这种有点消极的前提下,人们才会有被挑战的感觉,才会(终于)想动脑一下。而现在无论创作媒介、方法是什么,要让观众感觉到不舒适真的太难了,大家都佛系。
给那些我真正喜欢的人我都会祝他们健康
所以祝你健康!
文先
亲爱的纹瑄
关于朋友
1.
如果没有日常作为当然的基调,也没有情愫的牵扯为各种必然的不均匀(例如难免的权力关系)加诸先验的秩序或者转圜解套的依据,单纯为智性所驱动的友谊,到底可不可行?
当日常自有一套包覆性的轮廓(例如老同学、同事等等总之有个预先配备在那里让你们一起吃饭喝酒纯聊天那种)、当情人和闺蜜有私密情感来主持着情谊的持续高温(即,思考交锋无论比重如何,概念上它都是这段情感的附属配备),纯粹由创作和思考所启动的友谊,该如何继续下去?
这个问题的原型其实是,我们真的可能以一个绝对、完全、贯穿性的思考与实践/创作者,来界定完整的自我吗?就算像电影中那些斩断/失去一切人际关系,以致于彻底loner的特务、杀手,纯脑袋驱动的生命情状,真的可以很美吗?我的意思是,没有了日常那些腐蚀与腐烂,人可能是柔软的吗?没有了柔软、流动、可爱,这个角色还能是美的吗?
因为对理论的热爱,我曾很想走学术,或者,当黑格尔、康德、佛洛伊德、傅柯那样从无到有发动一个新概念的作家(不含尼采,尼采是艺术家),但哲学家的写作,概念再漂亮,就是少了“真正活过”的湿润和软黏,没有露水、青苔、月晕,也没有梦,即使是谈梦的理论书里也不会有梦,一个都没有。所以尽管艺术创作这一边,比如“纯文学”,有那么大块其实是弱智、反智、或者真就耽溺在享受气氛缺乏动机要hardcore地往前推进思索,我仍觉得我也只能在这里,真正的美在这里才是可能的。
至少对我来说,我无法真的让自己成为一个只有脑袋运转的人,基于美学上的理由。而也正是这样的理由,我无法想像可以拥有一段真空中的友谊,尽管我很期待,那就像是思考这件事有了一个实际的空间(如果一个人的密室思考中就是抽象的话),但这个空间真能在时间里持续吗?一期一会不叫朋友。
这是我总是过不去的纠结点。后来,当其实一个人思考也还过得去,我不再期待思考伙伴;若有暗香浮动的微恋爱、类恋爱顺道带来的哲学和艺术伙伴(然后随时就会因为感情不稳定而不了了之?)、偶尔相遇的交会迸发烟火,也就可以了。最后不得不是,思考归思考,朋友归朋友。
这个问题在我所谓的原型提问的解方是,我就创造一个以上的平行角色,每个都活出独立的人生。但朋友没办法这样不是吗?难道能彼此都创造角色,然后每一条线各自精准配对,多股编织地创造一段“什么都有”的友谊?
2.
开始了,要怎么停?
再度是个物理学意象:如果没有摩擦力,静者恒静,动者恒动。撇开前面谈到的沧海桑田的坠落,如果可以真用脑袋无重力移动,那什么时候会停下来?
我总是想要写这样一个剧本,里面只有两个人,没有故事与身世设定,没有背景,剧本从第一句话开始,那是寻常的一句话,然后第一句话引来了彼方的回应,就有了第二句话。对话启动,持续运转,像个永动机。我想写这样一个剧本,不为了他们谈的内容,而为了作为这样一个概念的范例/演示:“对话将永远继续下去”。而这件事应该要是剧场的本质(就算只是之一)。
(但我想我不会去写这个剧本,因为无论我可以创造多少角色,我仍以此一肉身拥有唯一一笔线性时间。我不要像福楼拜写布瓦尔和佩居榭,我不要那样把人生压印进那个我要创造的演示(谁来帮我诠释?那个诠释我会满意吗?))
在朋友这个题目上,尽管在经验里,关于与互相激荡思考的朋友之间,总是还不必烦恼“什么时候会停?会怎么停?”之前,就已经迎来了这样的困惑“啊怎么已经停了?”,毕竟我们就是活在一个巨大摩擦力的现实;尽管如此,我仍在脑中持续进行这样的思考实验。
一出永动机的对话。……先不谈这份友谊/对话的紧致张力所带来的感性上的意义(窒息感、争胜或至少是不能输的压力、在其中滋生柔软却不被允许发挥的羞赧……)、不谈表演上的洞察与微调(节奏、松紧、空隙浮现的不定性),我只先问,当这个对话无限地开展,则我们如何从中间具结意义,当所有的意义必定得有边界且建构由时序后端?而这不就是这桩友谊最重要的核心吗:创造“一个”(意味着已完成)新的讨论、论述、洞察?——不要告诉我“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我不是过程派的。
我想像在那乍看协调通顺的对话里,必须另起一双极清明的眼睛,才能在下一动开启前,断然收束有效的意义;这么一动接一动,似乎敞开的对话,就有了一丛与另一丛的边界,每一具收束出的意义,将可望平行展开新一层次的来回或累积。
但又回到现实,总是又回到现实,有如此能耐的彼此,谁不是挂念着创造一家之言?从哪里榨出的分秒月年,来实际操作这样的友谊,让那个排在自己创作的更前面?
3.
关于危险。
是的你说的太好了。
“……在当场惊觉我和观众之间的‘有互动’都是假动作,都是一场误会。……而现在无论创作媒介、方法是什么,要让观众感觉到不舒适真的太难了,大家都佛系。”
放在朋友的题目里:我敢不敢或愿不愿意,去为难我正对话的彼方,藉由将他置入真正的险境,激发出他的、与我们之间的潜力,从而让这出角力跳上新一层次的对垒?
我敢不敢去实践真正的危险?既然我认为危机确确实实就是转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巴塔耶式极限与越渡的、纯净而绝对的......然而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必须包含下一题:我愿不愿承受此一危险可能失控地耽误、污染我的思考与创作状态?与他人的任何绞缠,就是这么不透明,而我能为这个不透明付出什么代价?
与其问把他人陷入如何之危险(各种负面情绪),不如问,我能如何想像自己把他人陷入如何之危险?当我自己有700%的玻璃心,我如何可能不这样empathy他人的碎裂?当我乐于自虐地维持甚至强化自身的脆弱,只为了能够更精细地测量关于人与世界的各种幽微,我能真以为也可以如此试探挑衅他人,以至于与他分享险险飞过死亡后将揭露的真正深奥的开阔吗?......是的别人没有那么脆弱,但我可能就是那么脆弱。当震撼教育不知道有没有叫醒他们的同时,我已深陷我想像的剧场,因此耽误了我本来的安静和清明。
如你一样,我太着迷那个“假”与“演”,当这些事在真空中可以朝永恒逼去地幻化成华丽与完全的图景,但在现实中,那个很陡的摔落、很平庸的撞到墙,会瞬间消灭这些事原本可以有的生产力。而事实上别说他人准备好了没,我只问,我自己又是花了多久才准备好?而当我准备好了,我不其实也就不需要别人来对我做这件事了吗?
关于“假”与“演”我有一千万字想谈
所以只能先这样了!!
yours,
e

亲爱的乙烯,
3. 关于危险
延伸你的延伸,重新组装我们正在讨论的:和你一样,我也更相信黑暗面,因此这里的“朋友”与“empathy”都是被放在这个基础上来谈,因此我们会谈到危险,谈到赌注,谈到挑衅、脆弱、碎裂、自虐。没错,就如同你将朋友套进我们试着拆解的f(x)而得出的,这是个害人害己的手势。容我x=“朋友”再换一下变成x=“建立亲密关系(最、非常、无敌的那种)”,有个我今年在试解这个方程式时遭遇的撞墙经验:
我在五月和七月时,分别在台北和墨西哥城做了一个叫“跳河小说”的表演,当观众进来暗室的时候,我已经背对他们坐在一张书桌前,戴着耳机,桌上有水、黑咖啡、我的电脑接着投影幕。表演是这样:我会开始打一篇叫做《跳河小说》的短篇小说,打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按下delete逐字删除全文。跳河小说在此和大河小说的关系是杰克尔与海德。小说分成定义、材料、形式、内容四段,在解释的过程中有两桩自杀嵌在里面,一桩是个人的政治性自杀,一桩是一般的自杀,难堪的那种、懦弱的那种、我奶奶的那种。
小说行文的方式刻薄且假学究。我在演一个踩线的暴露狂,藉由对自己残忍来试着伤害观众。(修正一下上一段:创作其实也并不只是让自己得以转化世界填鸭给我的讯息而已,这也是个微型的个人的反抗,赌“一个人做作品”的动作是可能把某种外挂程式反向装载回那个该死的外面的,切断细小却最关键的一条脚筋,让人在“平常”上面跑的时候不自觉跌倒。我没有能力在现实中真正拆解、豢养出复数的我,只存在是创作者的我和不是创作者的我,因为只有少少的两个,我必须用到极大值,必须前者等于总体艺术,而不只是前者做的作品是总体艺术)表演结束,带着刚呕吐完轻飘飘的虚脱感,我等着有人藉着回应把我的努力跟赌注变俗,好比对着我问“这是真的发生的事吗”或是“你怎么可以消费你家的悲剧”或是“你身边真的有人自杀过所以你才做这个主题吗”这种。
两次表演的状况差很多:在台北的那场长度是两小时,可能是各种环节——场地、时间、布置、天气等等有的没的一一出错,当我战斗(这样的场景设定的好处是我可以非常专注)完毕之后回过头看到没什么人(三个?),多来的一些人正在准备等等一场扮装派对的道具。我非常非常挫败,有种花了一辈子准备一场告解然后发现墙的对面神父根本还没上班的感觉。在墨西哥城的那场长度是一小时,结束转头之后,发现整个空间都坐满人,据说整场表演所有人都很安静很专注地跟着我的投影幕,该空间的director跟我说 “I didn’t expect it to be so hardcore”,另一个认识的策展人跟我说 “I need time to digest”,后来又有一个人说 “I love the part when you modified the quote from Midnight's Children, the effect of the collage was so… so…(一个眼神)”。
我应该要很满意的。
目的似乎达成:有人被震惊了,有人因此思考了事情,甚至有人还了解了某些部分的形式游戏,我应该要很满意的,但我好像比台北那场更挫败了。(对面的神父说:我懂你,他看起来不是装的,但还是——)
2. 两种“停了”
我也不是过程派的,可能还重视结果到有点宿命论。如果永动并不是过程的无限延伸而就是结果,那有两个可怕的敌人,一是因为懒惰、没兴趣、没有爱了等现实因素摩擦力导致的停止;另一个则是被来来回回中的“我们一起到了!”给骗了,假性情投意合之后仍然继续的动作都只是同语反覆,其实也是停了。
要怎样才不会被骗?
但话说回来,我又真的有那么强的什么来贪婪贪婪本身吗?
3. 关于朋友
所以到底什么是朋友?
像你说的,除去场景交叠及私密情感造就的朋友,创作和思考够不够格就成立是“我”及“你”然后“我想和你交朋友”?老实说,一开始当想要找你对写,对写题目草拟之时,我原先假设的内容很单纯:我直观认为,最严格定义下的朋友是不可能以活人的样子存在的,因为活人会动、会变、会令人失望,因此没办法用诠释将之塑形成朋友的样子,换句话说,如果永恒之城是装朋友的容器,某某死人之永恒是因为被我定义为是圆是方,而不是客观典范的结果;但活人就是那种抓进来会一直要嘛自己想出去或是不断让人后悔将他抓进来后来决定放生的东西。所以原本只是想问你,你的永恒之城里住了谁,这样一个轻松谈朋友如家家酒实际上却不相信有这种东西的悲伤问题。
但后来,这篇对写成为不相信朋友之人的交朋友计划。我们试着调整虚构朋友(也就是你说的纯粹由创作和思考所启动的友谊,可能你会有更好的形容方式但姑且一用)与现实朋友的构成比重,我们让彼此作为活人的湿润和软黏进来,但比例不能比创作和思考多。我相信经验,但并不是因为经验的分享是能够创造出记得所有细节的接收对象,而是为了能够直接切入动机的共感。这是为什么我想讲表演两次“跳河小说”的事。我们试着以你写小说的(我观察到的)方法来做这个朋友实验?
祝你健康!
文先
亲爱的纹瑄
我在读你讲跳河小说的事时,因为一个误读,把框架框错了地方。其实你讲的是一个作品的移地展览,我却感觉看到了重演。
也就是说,明明情况是,你的作品是同一个,这个作品两次所获得的回应不同
当然也可以看成回应是作品的一部份,如此就是作品必然会有的迁变或不定性。但我却一个念头岔开,感觉到了这是一件事情发生两次,也还会再继续发生下去(重演的本质)(即,作品在时空中移动 vs. 同一个时空重复发生)。
而这两次(无数次),表面上不同,但其实仍是相同的,就像重演并不是影印机的产品,重演事实上诉诸或发生在人与他的世界的某种平行或错叠。
但就用这个误读为起点。对我来说,“重演”这件事的重要,就在于它的“不得不重演”、“终究还是回到重演”,而凸显这件事的,恰恰就在于那个环境已遽然变迁,但蕊芯/灵魂的部分,却(不得不)仍一模一样。
借用你的比喻就成了,告解将无数次重启,而教堂与神父却从来只是个幻影
这不是很low的那种“作品与读者或观众或论者或世界间关系”的问题,而是创作这件事如何凭空缔造了一处存在,这个存在将获得如何的性质。而当我们将某个自我(例如创作者身份/角色)界定为一出总体艺术,那会是怎样一种具体(降落于哪里的具体?)的存在?
......关于重演与孤独的问题先不谈。
很巧合的,你的作品刚好关于自杀和删除。顺着想下来,那不会也无法是一个算式上的回退,那将会是一个强加其上的白。而这个白,它或者就欲盖弥彰地反而强调了那些被删掉的东西,例如那个自杀前的活着、自杀的动机,又或者,它会是一个策略性的白:把所有事情都弄混,当无法辨别,就没有了原件,删除在某个意义上就成立了
我一直喜欢阿里巴巴那个故事,在所有门上打了X,由此就找不到被锁定打X的那一户。我也由此发想我对抗这所有东西的策略:当所有痛苦来自清明的心智,我能做的,可以是更多地歼灭那个清明。很合逻辑的作法。
或甚至其实也正是我在前面信中提到的,是否朋友,关于朋友的真正(一起)活过,得是出发由某种浑沌,所以我们会需要一个区间的胡乱抛掷闲聊,与其说是暖机、缓冲、解除心防,放在我们的例子,更像是将两桩独立而锐利的清明弄钝,然后我们可以开始“一起”些什么,是为朋友。
2.
关于朋友(却又非关上题的结尾。又或者有关?)
你说,“我们来用我们两个自己做个实验吧,不相信朋友之人的交朋友计划。”
但难道我们不是已经在这个实验或计划里了吗?或者说,不其实是非常合理的吗?把我们此刻的交往看成已经正在进行这个实验。
朋友是怎么开始的?
我们在一个夜晚相遇,不动声色却深刻地,彼此都感觉着对方是与自己好相像的人。或至少是这么宣称的。
我们并没有因此有接下来的联络,直到一个名为《我叫你们作“朋友”》计划,
然后我们开始给对方写信。
那样动员身心地写信,像是已经是朋友,或其实是写完了不得不、必然会成为朋友。就算只是这个区间的朋友。
那么,所以关于“朋友”的写作计划是个起点?还是那是个终点?
也就是我们事实上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开始这个演练:从谨慎的问候,到很快感到亲熟与安心。这中间为什么不会其实是快速地入戏?
我从哪一封信或哪个动作,跨进“建构朋友”的框架里?又自哪一刻起,入戏地浸淫,进入地真正成为这段友谊的一部份?
而这样的提问最令人不快的地方在于,我是否将在某一刻,轻易(或缺乏理路可厘清地)断开这整幢建构的任务。在这个现实里,从来就没有过你这个朋友
(分隔线)
以上是一种假想,却是不但合理、而且非常适合我们的假想。这像是Eco的书会有的情节。
但倘若我们要将那个创作的自己,刻镂为一个总体艺术,则不事实上就该做到这种程度的断然和忍心吗?在这样的时候,我会觉得,终究我没办法完整地实践一个我的理论里的角色。
yours,
e

亲爱的乙烯,
昨天一连看了五集《追缉炸弹客》,有个与剧情无关的部分却让我非常感动: FBI的人在分析炸弹客时,都相信这是个求学不顺遂、学历低因此恨学校要去炸学校的人,或是被航空公司怎么样因此要向他们报复的工人,只有主角在用forensic linguistics的分析方法工作过后,赌炸弹客一定是超聪明的知识份子,理由完全与报复无关;在炸弹客要用条件——刊登他的宣言在报纸VS继续放炸弹——来交换时,其他人都觉得其中有诈,只有主角觉得这就是他真正的目的。
有什么东西就怎么回推那人的模样,而不在分析时以常识绑架所有人行动的可能性,相信有人是真的将生存赌在抽象交换及意义生产的——我应该要修正寄给你第一封信的内容,让人绝望的不仅是大多数人太轻易将人视为天才,同时包含太轻易将人视为笨蛋,不相信“修补世界”是可以作为动机的,“求知”是可以作为动机的,“避免自己因为无聊而死”是可以作为动机的。
说不定这是朋友之难的某个关键理由:因为意识到各种事、各种人的动机都有(复数的)可能,所以每条线都可以被放大成无数缕交缠之后的结果,能不能做成这出无限套层的戏中戏也成为在面对作品、判断作品好坏的要点之一——但这个难在一般现实中处人时并无法成立,因为在一次一次与世界交手之后发现,太常只是自己的内心戏,复杂情况真正出现的机率少之又少。所以说不定那个“将两桩独立而锐利的清明弄钝”的动态其实是,让我们彼此可以还原到如同面对作品的小心翼翼,信任对方是复杂到自己必须生产新工具来理解、对话的,是之为弄钝。换句话说,交朋友在这样的前提下变成将非常重要的这段:
这不是很low的那种“作品与读者或观众或论者或世界间关系”的问题而是创作这件事如何凭空缔造了一处存在,这个存在将获得如何的性质。而当我们将某个自我(例如创作者身份/角色)界定为一出总体艺术,那会是怎样一种具体(降落于哪里的具体?)的存在?
——由自问转为理解对方的任务:你已是一出总体艺术,我要怎么认定你的性质,怎么理解你(在哪的)具体存在?
(你说的太好了:欲盖弥彰的白,之所以做自传跟自杀的命题就是这个叙事游戏,我能选择盖某些部分以反向强调这些部分,而每次盖的地方不同,整体都会结构性地被调整,你送给我一个非常精准的描述方式。活人不常有施行这种手法的机会,总会因为某种方式或因素一下子就太透明了,没有东西好遮。)
但你是不透明的,那些被删除者与被彰显者在你的感知上是同时被计算、处理的,你在意后面的后面还有没有后面。正因为我们的“朋友”以某种不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方式运作,基本上即使你是活人,仍然是个虚构的朋友。我想知道如果将“朋友”由虚构拉越界到现实会怎么样。因此即使如你所说,对于这个“朋友”写作计划的所有bug——戏不戏的bug、结果可能在命题之时被写就的bug⋯⋯早在开始的时候就都出现了,但如果将那群我们根本没能遇见的未知读者也计算在内,那么就算就算有一方太职业病(哈哈哈)地决定突然断开,一切于我仍然没有不“成功”,因为对他们而言,我们的对话将成为你说的那种欲盖弥彰的删除、策略性的白。
(分隔线)
但终究我也没办法那么那个就是了。
祝你健康!
文先
亲爱的纹瑄
关于“朋友之难的关键理由”
我刚结束替一个摄影展的导读,作者在作品中大量引入量子力学和德勒兹的差异/重复的哲学与元素。原本这两件事不一定会同时想到,但刚好因为他又是物理系毕业,又热爱德勒兹,然后把两个东西一次放进那系列作品里,我为了这个案子也把两件事放在一起想。
在过程中,我脑海一直闪现着某种……个体不懈地要“作为自己”与“成为自己”的意象,在量子力学那边是当无观测者时粒子硬是走完全部路径那种实践全部可能性的着魔,在德勒兹那边是不断创造差异、以建构/虚构差异、由此朝向某种“新”、却也是对上一刻做消解的进路。以我们的关注就是,“当历史还没放弃地要继续朝向、成为自己,则何时才能有一个进入的契机?”,“当那个锁定想成为朋友的彼方,还漶动不定,则一段关系该怎么深刻地编织起来?”
而事实上,在后来的日子,我确实更明显地感觉到某种漂浮。当娴熟了不断建构与切换,飞越地差异又差异,那么还会不会有一个平台,在那里一切都安心安静,甚至平稳到可以长出与另一人的关系,它将自给自足地变得丰饶......
当我认同你说的“……信任对方是复杂到自己必须生产新工具来理解、对话的。”的同时,我仍忍不住担忧着这个同一个时空将在何时裂解。当“动”对我们来说是那么理所当然,我们又怎么面对和掌握“不动”,而这和持续创造差异并不矛盾,因为某个意义而言,当差异越过了一个私密的奇点(sigularity),那于外呈现的就是一种不动,而友谊真能理所当然地宽容那某种无法穿透的不动吗?
其实我并不觉得我们之间存着任何一种“赌一把”(假如你的说法不是在创造某种戏剧化的话),我反而觉得那是万中选一的必然,万中选一到、必然到,会怀疑“真会发生这么好的事吗?”但因为整个建构的过程,例如我们并不拥有一个现成的脉络,例如我们跳过了寒暄问候就在一封接一封的长信里直接触碰一段友谊所能拥有的最深刻的部分,对我来说,与其说感觉到的是虚(构),不如说我在珍惜之余是认命的(一种非常通俗的感性)——不知道怎么获得的东西,或许也就无法知道它将怎么消失。但如果是这样也没关系。
话说回来,关于这个“朋友”的写作计划,我觉得完整呈现我们在这其中的试探、怀疑与确认,正是最后设而切题的(也就是说不需要只留下正式讨论朋友这件事的部分),然后我们或许可以各写一两个段落以一个收束的角度来评论这个计划的内容,即是再一次后设。……为什么想先把文章的事确定下来,是因为我在写信时,常常分不出是在演(不指虚假,而是预设了观众),还是真的是只成立在我们之间,我不是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是说许多时候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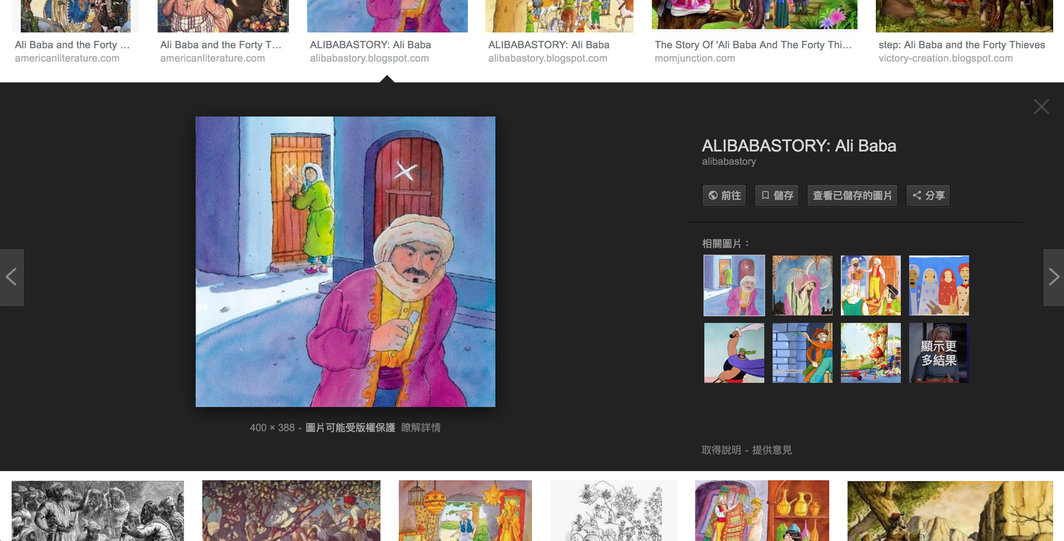
—————————————————————————————————
【后记|张纹瑄】
两件事。
第一件事,郭娟邀我写一篇围绕着empathy的文章,“中国翻译成‘共情’”,她说。看着这个字我一直在想,作为创作者照理说对这个字的感受跟理解上应该要是“没问题”的,但我却有点不舒适,因为不信任是我在接收所有讯息的基础音,因此这个无害的字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二件事,我跟以曦在第一次的对话后都有种“就是你了”的感觉,这种感觉清晰到没有什么其他形容词有必要用上,但又和我在第一件事的反应截然相反。其实我也搞不清楚这是因为(在接下共情稿子邀请后)我很想要有共情的感觉所以调整了接收器还怎样。但在结束这约莫一个月的信件往返后我能肯定的是,这种基于没朋友而讨论朋友、基于难以共情而讨论共情、基于不可能而讨论可能的方式的确就是一切的基本盘:在此之上我们才继续讨论历史,在此之上我们才继续讨论政治。
【后记|黄以曦】
事物是由什么组成的?把一个瞬间无限放大,会看到什么?
两个独立(甚至是过份独立)的个体,其间若有一桩关系的交织,那会怎样第一回合、第二回合、然后落定地开始长了出来?
这是一些科学的问题。
故事的开始,非关科学。
那是我总是喜欢的场景:一个夜晚、一个小酒馆、一场热心甚至急切的对话。
然后,分别后的路上,我想着这个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我们一定可以成为要好的朋友。
如果能十年、二十年前相遇就好了。我想。因为后来再也不曾交新朋友。那种“这是我的”,的好朋友。
几个礼拜后,我收到一封她的信,她说,我们来写一个朋友的企划。
像是写着写着这个企划就可以变朋友;像是为了这个共同创作我们可以演出诠释一种艺术与智识交往上的理想友谊;像是关于一段必定结束的偶然遭遇的一个比较特别的结尾。
像是通过“朋友”的暂且为名,我们将建构一处真正的起点,那条路嵌在彼此的人生当中,一个创作、思考同时有各种世俗的人生——我的意思是,有一个人,这样进来。
我其实希望这个共同作品里所呈现的从无到有的友谊是“假”的,那会是个细腻的科学计划。然而,无论事物是由什么组成,我总是直接就爱上了事物本身。
张纹瑄是一位生活在台中的艺术家。
黄以曦是一位生活在台北的作家。
文/ 张纹瑄,黄以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