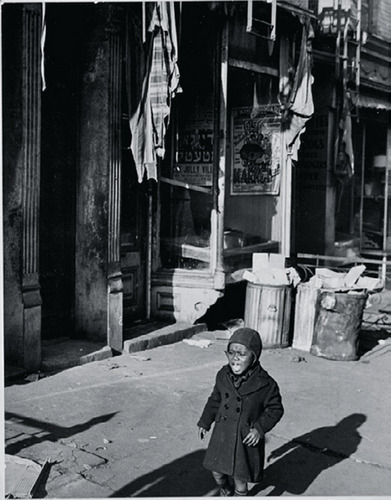玛丽•里德•凯利
斯蒂文•亨利•马多夫(Steven Henry Madoff)评玛丽•里德•凯利(Mary Reid Kelley)最近在Fredericks & Freiser展出的两件录像作品《萨迪,最悲哀的虐待狂》(Sadie, the Saddest Sadist, 2009)和《女王的英语》(The Queen’s English, 2008)。
关键词:饱和,自我封闭,双重性,双关语,语言的不稳定
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泥足深陷,伊朗又岌岌可危,如今,战争似乎与我们如影随形。越来越多的艺术作品和电影开始关注目前的危机,但玛丽•里德•凯利(Mary Reid Kelley)的录像却很特别,它把我们带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酷而又富有启示性的环境。所有关于武装冲突的现代记忆都难以摆脱世界大战的阴影,惊人的破坏速度,同时开火的多线战场,随之崩塌的国际秩序。破碎的统一让位于新文化的失范与社会动荡对旧有秩序的毁坏。这就是凯利两件近作《萨迪,最悲哀的虐待狂》(Sadie, the Saddest Sadist, 2009)和《女王的英语》(The Queen’s English, 2008)故事展开的背景。这两件集表演、诗歌、绘画于一体的作品主要讲述了大战期间在工业劳动、死亡和性中被推向附庸地位的两名女性的经历。
今年九月,凯利在Frederic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