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展览前两周,北京的p.m.2.5指数一度爆棚,当身处雾霾当中的人们都被压得倦意四起、忧心忡忡之时,大风大雨的到来最终让这场悲剧就此刹车。蓝天配合着清爽的阳光,好天气再次降临。而也就在这样幸运的节奏中,中央美术学院第二届CAFAM双年展“无形的手:策展作为立场”迎来了开幕的日子。不过,北京糟糕的天气还是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国外友人吓得不轻,当我问起YKON小组成员是否在前几日出门游玩时,他们的回答并不让我惊讶:“哦!布展实在太忙了,我们甚至连整个展览都还没顾上看,而且天气也……”,讲到这时他们无奈地摊了摊手,脸上意味深长的表情让我至今难忘。
由于本次双年展独特的年轻策展人选拔机制(策展专业指导教师为学术主持,各推荐一位策展专业优秀毕业生成为本届分双年展板块的策展人),让展览在开幕之前就赚足了眼球,神乎其神的展览分主题——“关于模糊性和其他游戏形式”,“《金枝》的密码——巫术、鬼混,与面孔的经济学”,“物的议会,抑或,在持续迷惑的好奇中漫步”等——更是将展览营造出悬疑小说般的诡异感。但也许是由于我的到场稍稍晚了些,设想中早已人满为患的大厅显得有些空荡,展厅也似乎还未苏醒。然而仅有一墙之隔的下沉式演讲厅中,发生于嘈杂的人声之中热闹的开幕嘉宾发言仪式,才真正宣告着展览的开幕。来自798艺术区的代表进行了热情的发言,他们作为此次央美双年展的赞助伙伴显然异常兴奋,大分贝的致辞让已经大步踏入展厅的我还以为是哪个愤怒的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发作。

相比于其他纸醉金迷的双年展景象,此次的央美双年展显得简单而清新,虽然王馆强大的融资能力确实帮助展览顺利运行,但是资金吃紧的状况也能从展览现场并不张扬的作品形态中能看出些端倪。国内的艺术家普遍在开幕半小时后鱼贯入场,随即又在人群密集的开幕大厅中迅速消失,几乎没有哪一件作品能引起他们的驻足——想想也是,作为资深业内人士,就算再有意思的作品看那么几眼也就足够了。而国外的参展艺术家和策展人们三五成群地坐在咖啡厅聊着天,仿佛和外面热闹的世界毫不相干。的确,他们真正的舞台并不在此处,而在此处他们也并不处于舞台的中央,体验式的心态倒让他们显得相当轻松。而在一楼摇摇欲坠、只能同时容纳十人的木盒子门口排队时,对面美术馆大厅的高墙上悬挂的六幅大型绘画让人有些诧异,但旁边正在热议的八卦更引起了我的兴趣。据说来自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策展人基特·哈蒙兹(Kit Hammonds)由于和馆方在布展期间合作不利,而在开展前夕大发雷霆。作为策展人中唯一身兼学术主持和策展人身份的男性,可怜的基特在随后的闲聊中抱怨说:“我甚至要亲手去给每件作品装框!”事实上,面对不可逃脱的策展行政,没人会感到轻松。此刻,基特已经走向了正在庆祝的欢乐人群中,看来对于曾经让人愤怒或痛苦的遭遇,我们总是健忘的。
二楼的展览布局相当紧凑,一件又一件精致的录像作品在展厅中几乎绵延不断,它们从各个角落裹挟着各种图像与声音向观者袭来,但这些还是让猝不及防的我看得有些发晕。唯一让人耳目一新的是洪子健与陈滢如的《特纳档案》,这一装置作品仿佛还原了某处末日研究现场,开着的台灯、有着微弱信号的仪器都似乎暗示着特纳的真实存在与随时在场。刚从被影像不断覆盖的展厅中走出,远处,身着绿色西装的俄罗斯艺术家瓦迪姆·扎哈罗夫(Vadim Zakharov)在人群中相当显眼,他正站在二楼分列的独立展厅外,给自己的作品拍摄着现场图片。金属硬币正从黑匣子中纷纷落下,引来不少参观者驻足捡拾,这件作品也是他威尼斯双年展项目的延续。“我就是想让他们拿走这些硬币!现在所有的艺术品的生产都是为了销售,艺术家、画廊、拍卖行和美术馆,整个系统都在强调钱。每当想到这样的事情,我就总会想起生活在苏联时期的我是多么自由,那时候我还是个书籍设计师!”似乎人人都在怀念,人们期待怀旧的当代在对过去的不断重访与回溯中通向未来,但目前为止,未来在这样的反复中只成为一种延迟的想象。健谈的扎哈罗夫除了谈到对自由的怀念外,说起此次的中国之行倒是有着同志般的亲切。“中国还存在着很多可能性,光是北京就有两个双年展,这在任何其他城市都是不可思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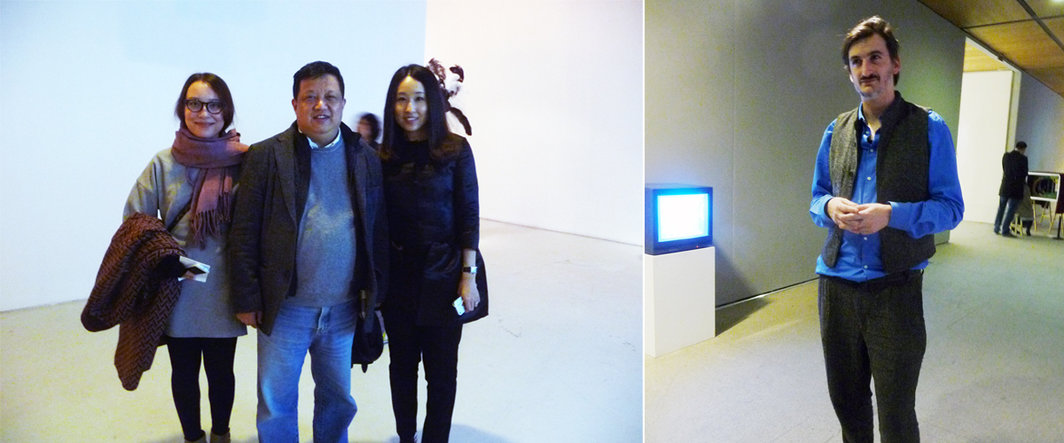
在不停有着不明生物靠近的走廊通道上,我遇见了维罗妮卡·瓦伦蒂尼(Veronica Valentini),对于此次策展人五女一男的状况她表示这很正常,并且也许预示着某种趋势。走上三楼,开放式的空间和强调互动的现场装置,让展场充满了游戏氛围,“游戏理论”作为有趣的切入点串联了展场的大半空间。然而游戏的形式并未在策略的层面上引导互动者进行主动思考,从而使展览成为一种有趣但是毫无营养的消遣。巨型蓝色集装箱垫着黑色枕木的强烈形式感让展览的空间分割迅速明晰,看上去有些复杂的展览内容却因为策展人马楠从杭州自带的工作团队,而让展览的布展过程相较于其他人而言进行得更为顺利,当然这也是中国美术学院近几年来集团作战的又一次演练。四楼策展谱系考空间前暂未开放,我也就随着折返的人群汇入了大厅中喧闹的人群中,并在保安闭馆的提醒中带着满心的好奇走出了美术馆——年轻的小雏鸟们扑闪着翅膀,奋力地飞向广阔的国际艺术天地,新新的展厅新新的作品和新新的人,一切都是新新的。谁能在当代艺术界清新的雾霾之中,调用无数双无形的手而最终看清远方的天际线呢?没人现在就想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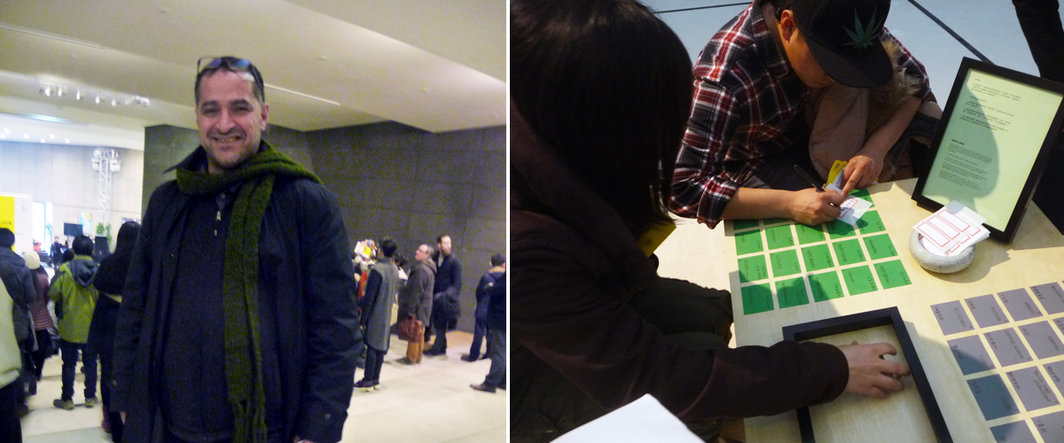
文/ 韩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