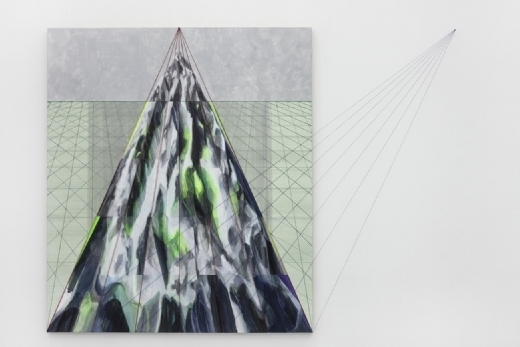颠簸的相遇
午后临近一点,急急忙忙赶往“思想·广场”活动现场,到了尤伦斯门口却被陆续驻足观望的人群差点挤了个趔趄。边猛地冲进大门,边回头张望,竟是明晃晃一排玛莎拉蒂!由于开讲在即,也没顾上随着兴奋的人群一同惊呼,便一头扎进已经人满为患的报告厅。
此刻诗人欧阳江河正襟危坐侃侃而谈,德国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正对着膝头摊开的笔记本沉着地书写着,以便化解欧阳江河繁复的中文对他造成的“折磨”(顾彬讲座中幽默的原话)。而在这位白发长者对面的桌上放着的是《新华字典》与《德汉汉德词典》两本小书,虽说向来德国人都以严谨著称,但是这般亲力示范还是让人觉得异常可爱。讲座探讨了语言作为人类存在方式在近现代转型中面临的挤压与改变,但同时也指出当代中国作家应该更多地摆脱文革伤痕与毛的影响,更多地发展出自己的语言。我们无法判断究竟今天中国文学是否病入膏肓,毕竟贾平凹似乎为我们带来了更多期盼,可让我更困惑的却是,当对母语的荒疏已然成为一种寻常人群的生活常态,如何从废墟文学之后的小时代让铺天盖地的段子手重新连接上汉语的文脉?或许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更多时间。
还未从上一场讲座中回过神来,便又急忙赶往下一主题《文化杂食现象》,趁着主讲人邱志杰还未到场向对面沙龙张望,不出所料,对史学感兴趣的听众并不算太多。随后艺术家邱志杰用惯常的机智幽默配合着粗糙的PPT讲稿,全程进行着自我神话的恢弘叙述。然而邱还是一如既往地具有煽动性,“我一直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不可分割为一种文化单位,人不是观念、立场、态度的工具。”仅此一句掷地有声之语虽不足以证明什么,但就这一种思想方法而言,的确可行,在场艺术与非艺术有志青年群情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