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午后临近一点,急急忙忙赶往“思想·广场”活动现场,到了尤伦斯门口却被陆续驻足观望的人群差点挤了个趔趄。边猛地冲进大门,边回头张望,竟是明晃晃一排玛莎拉蒂!由于开讲在即,也没顾上随着兴奋的人群一同惊呼,便一头扎进已经人满为患的报告厅。
此刻诗人欧阳江河正襟危坐侃侃而谈,德国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正对着膝头摊开的笔记本沉着地书写着,以便化解欧阳江河繁复的中文对他造成的“折磨”(顾彬讲座中幽默的原话)。而在这位白发长者对面的桌上放着的是《新华字典》与《德汉汉德词典》两本小书,虽说向来德国人都以严谨著称,但是这般亲力示范还是让人觉得异常可爱。讲座探讨了语言作为人类存在方式在近现代转型中面临的挤压与改变,但同时也指出当代中国作家应该更多地摆脱文革伤痕与毛的影响,更多地发展出自己的语言。我们无法判断究竟今天中国文学是否病入膏肓,毕竟贾平凹似乎为我们带来了更多期盼,可让我更困惑的却是,当对母语的荒疏已然成为一种寻常人群的生活常态,如何从废墟文学之后的小时代让铺天盖地的段子手重新连接上汉语的文脉?或许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更多时间。

还未从上一场讲座中回过神来,便又急忙赶往下一主题《文化杂食现象》,趁着主讲人邱志杰还未到场向对面沙龙张望,不出所料,对史学感兴趣的听众并不算太多。随后艺术家邱志杰用惯常的机智幽默配合着粗糙的PPT讲稿,全程进行着自我神话的恢弘叙述。然而邱还是一如既往地具有煽动性,“我一直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不可分割为一种文化单位,人不是观念、立场、态度的工具。”仅此一句掷地有声之语虽不足以证明什么,但就这一种思想方法而言,的确可行,在场艺术与非艺术有志青年群情振奋。
可惜的是,四个时间段内于不同空间内发生的对话与活动,因紧凑的安排而让期待全程参与的观众有些为难。当艺术家文慧的身体语言剧场活动现场进入到有趣的排练阶段之时,艺术家汪建伟与学者赵汀阳的智性对话的开始逼迫我提前抽身,虽然《可能性与必然性》的讲座题目学究气十足而又不免枯燥,但是整场两个小时的讲座过程几乎无人离席。从博尔赫斯到时间,从当代艺术到存在论,两位嘉宾的知识体系互相参照,在现场形成了非常良好的互动。讲座中不乏“骰子一掷”、“三个无关”、“飞鸟不动”等汪氏高频词,而赵汀阳以强大的文本解读能力从另一个更为基本的角度一一解锁了这些看上去诗意而生涩的文本概念。形而上的探讨却引起了台下执着观众的不满,他们期待的是两位老师将探讨的重点更多偏向于现实的社会生活。的确在资本、技术、服务所构成的权力社会之中,形而上的思考看上去缺乏“效率”,但其实现实不分“上”与“下”,而思考也不分“实”与“虚”。

穴位乐队的复出的消息放出后便备受瞩目,22日晚伴随着神秘的蓝色灯光,经历了20年离散之后又重新相聚的五位乐队成员终于迷幻登场,整场演出既有《微不足道》、《魂系归来》等经典曲目,又不乏与冯梦波、汪建伟、颜磊等艺术家合作的新近作品,虽然并未上演振臂高呼全体合唱的桥段,但是全场观众还是在不断地登台与谢幕中陷入连续的狂欢。作为“思想·广场”中最为特别的一环,名为“是或者不是,这是个问题”的演出单元企图通过在当代新纪元音乐中找寻到通俗文化或流行音乐与当代艺术之间的连接通道。
秋意浓烈的晚风吹起之时,聚集的人群就会离散开去。广场究竟是虚拟的意象还是思想的漫步?亦或是杜拉斯在《广场》中所讲述的“偶然的相遇”?在惊叹媒体的力量在今天如此强大之余,其实可能更多的疑惑也由此诞生,作为能够调动各方能量的中介,媒体在今天是否能自觉地推进一种更为深层与自由的发声?社会是否也因此借由媒体的视角可以延伸为复杂而丰盈的无墙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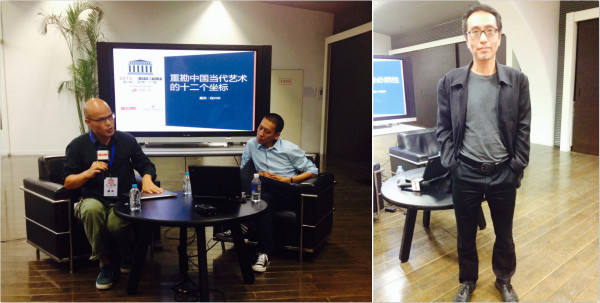



文/ 韩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