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yprien Gaillar, The Arena and the Wasteland, 2008,铜和混凝土材料,装置,柏林市立雕塑公园。来自"When Things Cast No Shadow”。
第五届柏林双年展
如今,双年展的模式对于当代艺术的决定性影响,比任何一场展览来得都要深刻,但这样的展览,也由于其服务于文化和本地政治的原因而受到批评。这种大规模的展览,当下的趋势是日益强调后概念性的创作实践,这种实践对特殊城市和地区的特殊场所的历史、经济、地缘政治进行透析,做出回应,Julian Stallabrass在其《艺术的合而为一:当代艺术的故事》(2004)中,进行了一番评述,认为双年展“以原始的竞争以求得在全球市场赢得一席之地”,对一个城市所起的作用,就好像“壁炉上的一幅毕加索之于一个烟草执行官”一样,它“不仅体现了并且也活泛地宣传了全球化的特点”。

第五届柏林双年展的策展人Adam Szymczyk和Elena Filipovic似乎更清楚这种对其本质上的批评;实际上,在双年展的宣传册上,他们近乎道歉般地解释,“双年展并不是当代文化盛事的一部份,”且补充道,“它属于一个特别的秩序。”展览本身,从局部上讲,试图以其丰富性体现出“双年展文化”的惯常特征,很快,德国媒体副刊上的很多批评家就撰文抱怨其不够大胆,干燥乏味,甚至展览本身,作为一个整体,也不经意地表现出其对宏大场面的渴望,毫无疑问,同样的批评者对此很快就会做出谴责。Szymczyk和Filipovic的展览汇集了众多相对不出名的艺术家,尤其是年轻的欧洲人,这是特点其一,但也许更为突出的是,双年展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通常的在“白昼”进行的项目,另一部分是晚间进行的活动,包括60场展览,表演,艺术家讲话,电影放映等等,可统称为“夜间”项目。这些活动,例如献给Lucan的“电视”(“Télévision” ), “飘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尘埃”(“The Dust that Floats Between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或者克罗地亚战后时期的先锋—-可归结于将双年展扩大成一个文化宣言的冲动,据策展人所说,是“防止完全可见性的文化垄断,且是防止将作品全部物质化”。无论他们的主题是多么特别,然而,值得疑问的是,一方面,这些夜间的活动,是否真的是对传统的场面的挑战,而非将“批判”的诉求灌输于它,而这种诉求在我们这个非物质化劳动的后福特主义时代又是非常需要的。另一方面,它并未发觉,评判的姿态,甚至是那些看起来反对将文化活动化的批评,也一直且已经处于了被同化的危险之中—它们正被同化成都市景观下的买卖活动,而这也是大多数双年展的特征。
不管怎样,在“白昼”进行的项目中,人们不禁注意到,Szymczyk和Filipovic已在自觉地避免他们的前任在2006年所行使的那一套方法。当时, Maurizio Cattelan, Massimiliano Gioni和Ali Subotnick精心安排了一场类似宗教游行般的活动,将参观者从教堂带到曾经的犹太女孩学校,再到墓地,每一步,人们都不得不直面关乎人类命运这样的问题。Szymczyk与Filipovic在城市的不同地方也安排了四个场所,很显然,他们希望双年展的参观者能在柏林四处走动,“但是”,他们说,“没必要去那些油漆剥落或处于废墟状态的历史场所。”所以,“白昼”项目中的地点,更强调的是柏林的战后时期和后柏林墙时期的当代柏林,而非试图营造一种近乎荒唐的历史氛围。例如,在Schinkel 展馆进行了一系列专题展,这是一个塔形体,它混合了社会主义者的现代主义和东柏林菩提树下大街上太子宫1969年扩建的新古典主义风格。而“白昼”其余的项目则分散在以下各处:Kunst-Werke当代艺术学院举行,这也是柏林双年展的传统大本营;1968年的新国立美术馆—Mies van der Rohe晚期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 在Mitte和Kreuzberg之间的柏林墙前“死亡地带”上的空地,这里也于2006年11月由艺术团体 KUNSTrePUBLIK改造成的柏林市中雕塑公园。

根据双年展的“简短指引”,最后的无人之地这个场所,“不仅是柏林墙留下的一个伤疤—对动荡的过去的提醒—-同时也是对萧条经济下城市化发展失败的一个纪念,是投资者狂想奢望的所在之地。”但是,这部分展览确是最薄弱的的环节,甚或是其最大的失败。策展人似乎过于依赖这里的独特之处和自我证明性,这是有悖于他们“避免废墟之地”的展览宣言的。雕塑公园中的许多雕塑作品,看起来就像是“出其不意”的作品,与它们所安放的地点没有任何关系。确实如此,如波兰艺术家Ania Molska用金属和木头构筑的作品,在她在Kunst-Werk的电影作品W=F*s (work), 2008中也出现过,而那里至少具有寓意性,能激起人们对俄国先锋和后共产主义波兰背景下,英勇般的体力劳动场面产生反映。像这种类似权宜之计的临时替代品,最多可被理解为是对“公共领域内的艺术”所面临的危机进行的评判。
人们不禁意识到,双年展中的公共艺术项目,作为对废弃场所的一种临时解决方法,对当代艺术重新进行解码。这些作品承担着与地点的特殊性产生关联的需要,作为比较,与柏林的历史趋向了一种例证而非反思的关系,自身消耗殆尽,它们所呈现的身份位置据称在此得到了证明。在Cyprien Gaillard的装置The Arena and the Wasteland, 2008中,柱子上一排排强光灯华丽地照耀了堆着杂草和垃圾的雕塑公园,似乎令人想起了死亡地带的监视器,同时,也表现这里作为房地产投机的一个地点,依然是一片未开发之地。同样,将特殊地点以简单主义的模式进行表达,在挪威艺术家Lars Laumann 2008的电影装置Berlinmuren中,也可以看到,其作品被安置在一个可以找到残砾破瓦之地,讲述了一个“物体化”的女人在1997年嫁给了柏林墙的故事,在柏林墙被推倒的19年中,她一直在哀叹它的倒掉。

与双年展文化唱反调的另一举措是在Schinkel展厅的一系列展览,它们于双年展正式开幕的两个星期前就已经开始了,而在双年展闭幕后的两个星期才结束,策展人称,这样做意在“颠覆以往的只有一个辉煌的开幕和谢幕的传统。”而这部分的展览本身也不是典型的双年展模式:每场展览中,一个年轻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出现在双年展的其它地方)都要展出对他或她的创作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的前辈艺术家的作品—-Szymczyk和Filipovic认为这些人处于“反现代主义的位置”。在Schinkel展厅的第一个展览题目为“时钟里的灯”,由柏林艺术家Nairy Baghramian 组织,选择的作品是由瑞士设计师Janette Laverrière于1989年到2008年之间创作的“镜子作品”,利用巴黎的Laverrière公寓作为基点,两位艺术家共同合作,用一只小箱子,一个铝制地面,彩色的墙,构筑了一个无顶的建筑,内里和外在体现了Laverrière所创作的由木头、金属、反光地面所创作的作品。而其中一些作品的前面,近乎有着后超现实主义面貌的百叶窗则抵消了作品作为镜子的功能;Laverrière的题目其实不时参照着一些特殊的人物和现代文学艺术的典范作品(如《爱丽思梦游仙境》)。这个装置的里面包括一个书架,架上是来自Laverrière 图书馆的一些书,从中可对她多变视野的现实依据得以一窥。

这一系列由艺术家策划的展览,是对艺术家的艺术家的致敬,它们以浓缩的形式展现了双年展整体的操作手法。同时,宣传册也是一个大部头的册子,不仅收录了如Beatriz Colomina 和 Georges Didi-Huberman 关于建筑和城市理论的文章,还放上了一长串的由所有参展艺术家提供的“原材料”—即艺术家的艺术探讨和作品,以及Francis Ponge, Henry Green, Robert Walser和其他人的文学作品。如果说,Szymczyk和Filipovic 在他们的撰文中,强调他们的初衷并不是围绕内容决定结果来组织展览,但显而易见的是,这届柏林双年展—甚至它的题目,‘When Things Cast No Shadow”, 依然唤起了一种对历史表征的比喻—反映了当代艺术先进对现代主义刻板的语汇的兴趣,重温了相随而生的对艺术自治权的渴望。这些关注在去年饱受非议的12届文献展中得以充分体现,但无论怎样,展览的大部分强调的是高度现代主义艺术的抽象和前现代审美学之间形态上的相似,Szymczyk和Filipovic 推出的项目,通过对特殊历史时刻和艺术的现代主义和现代性的审美潮流的自由的参照指涉,继续将这份与历史遗迹的交汇和展览的地点连在了一起。
这本身也许反映出今日艺术更为广阔的潮流。艺术史学家、评论家、策展人Helmut Draxler写过,“实际上,在每一处,处境和参照物之间的关系都在讨论之中,”将“处境”定义为“不同的空间关系,几乎每件当代作品世上都依照着所处的空间外貌进行创造”,而“参照物”形容为“各种暗示,名称,引证,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代艺术的交流代码。”在这种观察的背景下,人们甚至会提到当代艺术中指涉主义的普遍式样,一种将参照物和和前辈艺术家某些作品结合在一起的艺术模式,一种常规艺术领域之外的历史插曲,理论写作和审美密码的巨大并列。这届柏林双年展,虽然在理论上或策展方法并没有对这个影射和引用的过程进行解析,但从其刻板性和多产性的体现手法上,它依然为当代艺术的指涉主义的流通,提供了充分的审视评估的契机。
![Nairy Baghramian,《破裂的圆柱[1871]》,2008,金属,来自"When Things Cast No Shadow”,新国立美术馆。](http://www.artforum.com.cn/uploads/upload.000/id00756/article04.jpg)
对现代主义反动的历史和进步潮流的指涉,在Kunst-Werke处处表现得很明显。丹麦艺术家Pushwagner的一系列绘画Soft City,1969–75, 描述了一个城市的居民持续雷同的行为,这里的街道无尽头,这里的建筑是野兽派的建筑。在150多幅铅笔素描中,作品表现了Soft City的居民在兵工业和政权中,进行着重复的工作,或者涉及了训练有素的消费主义。这幅反乌托邦的景象辩证呼应的是David Maljkovic 的《这些天所失去的记忆》(2006-2008),其中,一系列的大学和一个录像表现的60年代南斯拉夫现代主义者乌托邦主义的魂灵。在由绿色建筑夹板做成的结构中,依稀可见的序列号似乎是影射结构主义的风纪。这位Croatian艺术家将Zagreb世博会已被遗弃的旧址和它全盛时期的新闻剪报和照片汇集到了一起,今日冷静的透视对应的是昔日对进步与繁荣的向往。似乎为了讽喻表达这种非同时性的状况,紧挨着这些照片的录相表现的是博览会意大利展厅上小小的新车边摆着僵硬姿势的模特,以此重铸了未来主义汽车展厅。
而在Kunst-Werke, 指向历史和政治的作品则独立于其展出的场所新国立美术馆, 这也是迄今为止这届双年展最具说服力的部分,它为展出的作品提供了一个颇具效果的空间和历史脉络。Mies van der Rohe的钢与玻璃制成的正方体是创造环境与参照物之间自我反射关系的艺术的理想之地,一方面作为此处的建筑界限被解读,另一方面,体现了现代主义作品的激情。但有时,在这里我们也遇到了这样的作品:对参照物的应用,只是进行了自我合法化。这在那排旗帜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罗马尼亚艺术家Daniel Knorr于2008年创作的作品《国立美术馆》被安置在这座建筑的平整的屋顶边缘处。这些旗帜令人想起色场绘画,它们实际上是柏林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的旗帜的复制品,且不说其完全的保守,Knorr的作品最终似乎只是表明即使是现代主义者的抽象也可以以反进步的语汇进行解读。作品与它展出之地之间的微弱联系,只是通过它的题目误导的暗示才得以表达得清晰起来,这些旗帜代表的是国家民族,而与建筑本身没有更深的可比性。而室内,Susanne M. Winterling以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运用Mies van der Rohe的构思,将国立美术馆两个对称的储衣间,融合到她的作品Eileen Gray, The Jewel and Troubled Water, 2008中去。这件形式上具有说服力的作品包括一个投影仪,一个建筑模型,以及图片,每一个在相对的衣帽间都能找到对应体,就好像镜像一样。她浓缩的抽象电影是以美术馆的厚玻璃板为形的,公然挑战了建筑师强调透明的目的,也许这是在特殊地点上,对估测和意外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简明的评论,但Winterling所指的不仅是爱尔兰建筑设计师 Eileen Gray,还有她对 Le Corbusier, 现代设计和Kenneth Anger的关系,结果作品过度地承载了文化上受到禁止的、被批评为可笑的参照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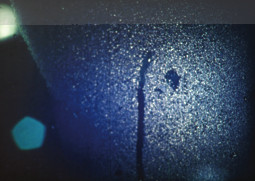
在国家艺术馆的一层角落处, Marc Camille Chaimowicz 将这个空间改造成 For MvR, 2008.
一个大蕾丝帘从玻璃墙前垂下来,通风井支撑的大理石覆盖的是墙纸图案,而它们本身和 Connecticut的Wadsworth Atheneum 艺术馆的室内装修图也再度出现在邻近的拼贴画中。这部作品以极简主义者的肃穆感与早期的现代家居风格的丰富性进行了比较。Rosalind Nashashibi和 Lucy Skaer在他们合作的作品 Pygmalion, 2008中,同样使用了帘子将博物馆分成一段一段,聚焦的是Henri Matisse为威尼斯 Chapelle du Rosaire 设计的教士服,用一系列黏土做成的马腿模型(其“原版”可在一个 Plexiglas马赛克地板上找到)加上复制的书页,将这些装束和焕发出生命的远古神秘雕像结合在一起,这个过程中也体现了现代抽象派和所运用的技艺之间的内在关系,它毅然放弃了融合极简主义风格——这种风格依赖太多的与设计史有关的近期作品。
展览中,在创作指涉上,最具密度的作品就在场馆的后方:Baghramian的雕塑La Colonne cassée (1871), 2008, 这是两个带有圆形小切口的、涂了黑漆的长方形盘子,较低的底儿弯成了一定的角度,通过艺术馆玻璃墙面映照着彼此,第一眼看上去,人们会产生错觉,以为这是带光谱的镜像。这两部分似乎仅靠白色的钢板支撑,若非如此,它们肯定就会碰到玻璃而碎掉。作品动静结合的构思,暗示着后极简主义雕塑,也强调了 Mies van der Rohe所运用的材料的脆弱性,参观者的视线穿过精心安排的切口,得以反射,而不是像建筑师希望的那样,穿过玻璃墙面。此外,这部作品也参照了Laverrière的镜子作品 La Commune, hommage à Louise Michel, 2001, 这件作品也有着同样的切口,令人想起了子弹洞,是对参加了促使1871年巴黎公社的起义的一名不是很有名的女性活跃分子的致敬,而印有Baghramian的题目的圆柱则在旺多姆广场被推倒。关键的是,对Laverrière和 Michel的双重参照不仅是独特的兴趣点所在,它也被Baghramian创造的作品从外观上进行了写照,无疑,体制化的当代艺术的独特背景不会很容易仅仅通过指涉的形式主义方式就被超越,在对一件抽象的雕塑的现象学经验上,新国立艺术馆和它怀有的建筑理想如何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即现代主义的一部分而产生作用——现代主义扩展的进步逻辑又总是预先假定为特别技巧的必要条件——在此,这点已经很明显了。正是这种具有批判性的反身指示密度的创作形式,为本年度的柏林双年展带来了一些创作上真正颇丰的时刻。
作者André Rottmann为柏林的艺术史学家,评论家,艺术杂志Texte zur Kunst的编辑。
译/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