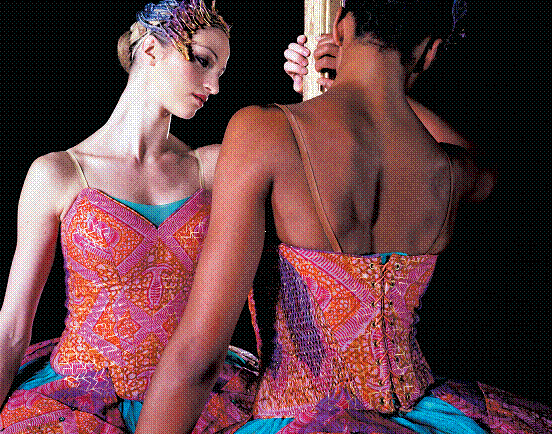
尹卡•索尼贝尔、《奥戴尔和奥黛特》、2005、 彩色录像剧照、14分28秒。
尹卡•索尼贝尔
尹卡•索尼贝尔(Yinka Shonibare)经常称他自己为“之内的外来者”。这种称谓很恰当,艺术家在纽约布鲁克林的艺术生涯中期回顾中,入口处既呈现出欲拒还迎的态势。《休闲女性》(2001),以张开双臂的、等身长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人物来欢迎观众,似乎是在引导着我们进入她的领土。而她的另一只手则抓住了三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外国猫的皮带,启蒙者们殖民、分化和驯服自然界的欲望所带来的暴力性在此彰显无疑。索尼贝尔将这种模棱两可性延伸到人物的民族身份上,标志性的手法就是塑造一些无头人,女人穿上荷兰蜡染棉布,这也是艺术家特有的材料,来源不明:它实际上是一种“非洲”材料,由荷兰人根据印度的设计而制作,最后再卖到西非市场。印花的布料,部分地表现了整个错位的文化消费,民族与外来、内与外的混杂。如纤维玻璃做成的猫科动物,似乎已经超越了雕塑的界限,索尼贝尔唤醒了人们对启蒙者美学的过度“他者化”的认识—-疆界性,修饰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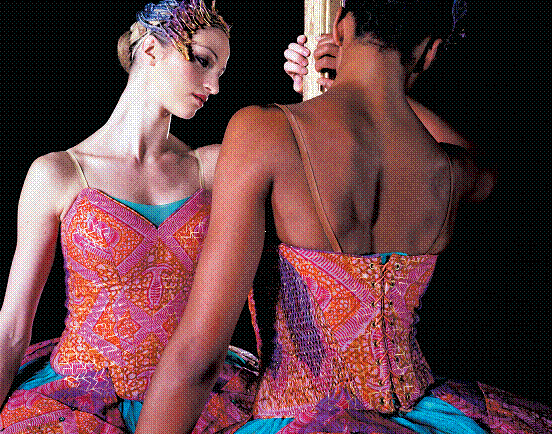
展览对边缘化-中心化进行了微妙的概述,提出了休闲与权势、掠夺与商业、欧洲殖民主义和非洲的身份之间的历史关联。由瑞秋肯特(Rachel Kent)为悉尼当代艺术馆组织的展览,精心所选的雕塑装置,摄影,录像,油画,无一不体现了艺术家创作的亮点所在,其中包括早期的荷兰蜡染布制成的方形油画—-以“非洲化”的描述对现代主义抽象进行微妙的渗透—-还有近期对启蒙思想家和他们的思想进行探索的作品。
在布鲁克林,展览延伸到了博物馆特有的年代性房间里,一件崭新的具有多重局部的装置《父母努力工作所以我才能玩》(2009),揭示了艺术家背后神秘的创作行为。很多附加的修饰就好像恶作剧一样,在重建的Trippe House的小卧房里,他放入了一个小男孩的雕像,还是无头,身着蜡染衣裳,这个马里兰的房屋,向前可追溯到1730年,人们不禁想起了另一个关于马里兰生活场景的那位被奴役的非洲仆人,在Henry Darnall III ca, 1710中,殖民的美国的一位艺术家加斯特斯•恩格哈(Justus Engelhardt)描绘了土著家庭的年轻子嗣。索尼贝尔的这一笔不仅提出了美国作为前殖民地前蓄奴国家的双重身份,同时又再次证实了艺术家对于补充添加手段的喜好。这位艺术家,在自己的名字后正式地添加了字尾,几乎盖过了自己的真正身份: MBE,是指2004年他被授予不列颠帝国勋章这一称号。
并置与添加的手法在这场被轻度删减的回顾展中,发挥了不小作用。《黑金II》(2006),这件一面墙的装置,上面是二十五幅圆形的荷兰蜡染油画,紧挨着《抢夺非洲》(Scramble for Africa, 2003), 如此安排的意义不言自明,索尼贝尔的关于1884-1885的柏林会议的装置,将欧洲在19世纪对非洲的侵略以图形化的方式进行了诠释。当时,金子和其它自然资源促使欧洲人来到了非洲,尤其是“金海岸”,“黑金”,成为后殖民时期的一个重要动机。索尼贝尔的无头男士们围绕圆桌坐下,桌上是非洲大陆的图,而两件作品中的荷兰蜡染布料指向了殖民地对于帝国所在地的双向的文化影响。两件作品产生了奇异的效果,有力地控制了洞穴状的超大展馆。
《奥戴尔和奥黛特》(Odile and Odette, 2005)是索尼贝尔的第二个录像作品,体现了近来他对精神内在的观察与探索。两名芭蕾舞者,一黑一白,身穿荷兰蜡染布做成的衣裙,彼此相互映照。当她们在镜子前跳舞或摆姿势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她们的呼吸声。我们看到了那些不安的私密性时刻,思索地注视着彼此,咬着指甲,或者擦拭着裙子上的什么东西。当我们看到两个舞者相对起舞时,索尼贝尔让我们开始思考:究竟谁是谁的映像?以柴可夫斯基《天鹅湖》中的角色为原型,《奥戴尔和奥黛特》似乎成为作者1995年的装置《一个像你的女孩怎么才能成为一个像你的人呢》(How Does a Girl Like You Get to Be a Girl like You?)的后续,在这件作品中,三个无头的雕塑小人,身着荷兰蜡染做成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裙子,作品还被戏谑地起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名字。虽然这件老作品不在展览中,但是名字却令人怀念,它体现了索尼贝尔冒险精神中不停歇的质疑精神:对于决定身份、内外领域的文化影响的共通性的质疑。
索尼贝尔将自己成为“与学院有关的特洛伊木马”。但是他不仅从内部颠覆了学院化的机构,而且也从外部下手,对其进行重塑与选择—-他的回顾展多变的行程中恰好体现了这一点——-一座当代艺术博物馆,一座如百科全书般的博物馆,一座非洲艺术博物馆。这位博学的艺术家展现了当内与外、中心与边缘不再清晰时,颠覆将成为何种态势。
展览于2009年11月11日到2010年3月7日在华盛顿的非洲艺术国家博物馆展出。
作者萨拉•路易斯(Sarah Lewis)为纽约和纽哈文的作家,策展人。
译/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