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Allora & Calzadilla, 《停下,修葺,准备:在一架预制钢琴上的“欢乐颂”变奏》(Stop, Repair, Prepare: Variations on “Ode to Joy” for a Prepared Piano)(慕尼黑艺术馆和纽约Gladstone画廊)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里的《欢乐颂》(Ode to Joy)不仅与浪漫的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紧密相关,同当代政治也有重要联系。(欧盟盟歌就是它。)在Allora & Calzadilla的作品《停下,修葺,准备:在一架预制钢琴上的“欢乐颂”变奏》中,六名钢琴师轮流反复弹奏这首名曲。琴身中间被挖了一个洞,钢琴师就站在这个洞里,因此他们是背向琴键的。钢琴脚上还装有滚轮;每位音乐家在弹奏的时候可以推着钢琴在展厅到处走。这是艺术家2008年为慕尼黑美术馆创作的作品,由Julienne Lorz策划(我看到它是2009年年初在纽约)。作品探讨了艺术与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欢乐颂》的磅礴气势到了这儿不复存在,因为改造过程中切掉了两根弦,所以整首曲子少了两个八度。

2. 米开朗基罗•皮斯特莱托(Michelangelo Pistoletto)新的生物建筑(Biella,意大利)
皮斯特莱托的Cittadellarte——一个致力于责任与可持续性的社区中心、大学、艺术家驻村项目、集体艺术作品——今年在皮斯特莱托的家乡开了两个新空间。空间位于经过改造的旧厂房内,厂房屋顶上种了草皮,墙壁也改成了泥土制造,这样一来,再热再闷的天,身处其中也会感觉凉意阵阵。空间里的机构包括一个生物建筑和设计办公室(N.O.V.A. Civitas)和一个天然和再生材料开发办公室(Prodotti di Svolta),开发的是将科学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的产品。

3. 克拉拉•利登(Klara Liden),“别再来”(Never Come Back)(Kunsthalle Fridericianum,卡塞尔)
利登这件对抗意味强烈的作品直指白立方内部的观看体验。个展“别再来”(Rein Wolf策划)几乎完全取消了传统的观展体验。艺术家在主展厅建造了一座巨大的“房中房”;从外面看似乎还在“施工中”。内部低矮的天花板是用Sheetrock石膏板做的,灯都装在靠近地板的位置,上面覆盖着沥青纸——一种通常用在房顶上的材料。外面放着一堆压缩垃圾,上面是若干监视器,播放着艺术家的两部录像作品:一部里是艺术家夜里往河里扔石头的图像,另一部里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柏林的总部(现在已经搬空,墙上画满了涂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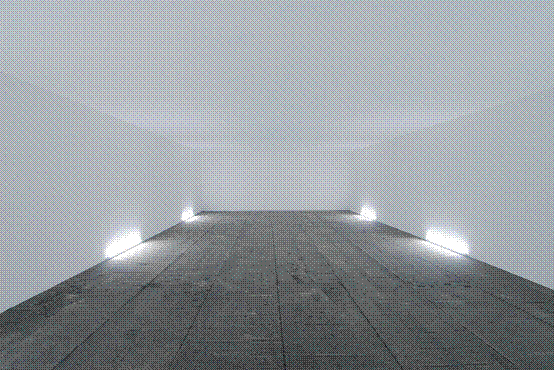
4. “罗琴科和波波娃:定义构成主义”(Rodchenko and Popova: Defining Constructivism)(泰特现代美术馆,伦敦)
这场由Margarita Tupitsyn和Vincente Todoli策划的展览信息含量丰富,梳理了亚历山大•罗琴科(Aleksandr Rodchenko) 和柳博夫•波波娃(Liubov Popova)两位俄罗斯最具影响力的前卫艺术家乐观、富有革命精神的作品。两人通过“操控”日常生活对艺术品的独立性提出了挑战。
5. 奈德•索拉科夫,“(不带面具的)情感”(Ned Solakov, “Emotions [without masks]”)(达姆城Mathildenhohe,德国)
索拉科夫在“(不带面具的)情感”展览上以“罢工”的形式反对了过度视觉化的景观和拿无形劳动做交易的行为。达姆城是他个人回顾展的第三站,这一次,(据他画在墙上的漫画叙述)索拉科夫觉得自己已经筋疲力尽,不想按照策展人Ralf Beil用模型规划好的详细布局布展。相反,他把运送作品的箱子原封不动地放在画廊展厅,在旁边配上幽默的小草图。这种诗意的姿态似乎回过头纠缠着该空间上一个展览残余的展示体系(“面具:从罗丹到毕加索的面孔变形记”)。和录事巴比托(Bartleby the Scrivener,梅尔维尔小说里的人物)一样,索拉科夫不给任何借口——他就是不愿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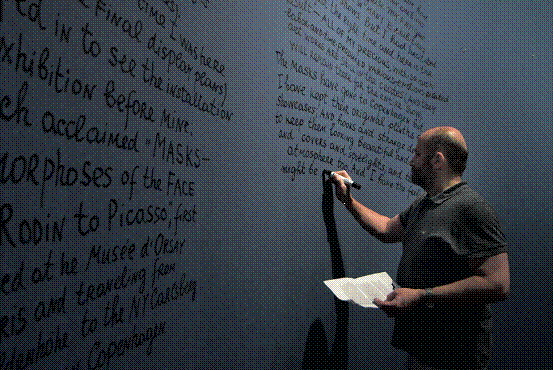
6. 雷娜塔•卢卡斯(Renata Lucas),《威尼斯旅行箱》(Venice Suitcase),(威尼斯双年展)
卢卡斯的《威尼斯旅行箱》——绿园城堡正门入口处的一段沥青路——看上去如此平常和熟悉,以致于许多参观者都没注意到这件作品。但同时,沥青路的存在又那么强烈和超现实:在这座不以汽车为交通工具的城市里,沥青是一种很少见的东西。然而,如今威尼斯的运河里油迹斑斑,所以卢卡斯的作品其实用了差不多同样的物质(沥青是精炼原油的副产品之一),只不过将其变成了文化物品而已。
7. 哈里斯•埃帕米诺达(Haris Epaminonda),《斑马》(Zebra),(沙加双年展)
在第九届沙加双年展(策展人:Isabel Carlos)的暗室里,我坐在一张剧照前,听着反复播放的巴赫大提琴曲,仔细端详画面的内容:三个男人制服一头斑马,身后停着一辆吉普车。这是埃帕米诺达2006年的投影作品。一块看似颜料笔刷上去的彩色挡在斑马的脖子处。实际上,色块只是埃帕米诺达在原片里发现的一处瑕疵,但这貌似拼贴的抽象擦痕令整个画面梦境般的戏剧感更加强烈。这件作品似乎在探讨为单幅图像重新注入意义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在悬置的时刻中发现叙事,发现激情,发现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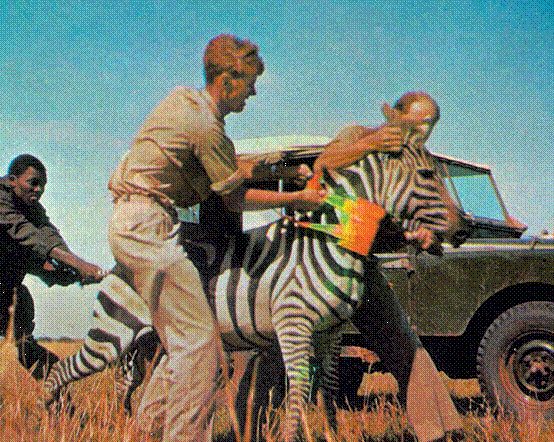
8. 陶马什•圣奥比,又名塔马什•圣约比(Tamas St. Auby, aka Tamás Szentjóby),《半人半马怪》(Kentaur),(伊斯坦布尔双年展)
匈牙利诗人、音乐家、行为艺术家、激浪派成员圣约比曾经说过:“艺术就是被禁止之物”。他在自己立场激进的影片《半人半马怪》里对这句话可谓身体力行。这部长达三十六分钟的蒙太奇电影刚刚拍完就被禁止公映,该片讲述了独裁政权下工作的政治:工人日常生活的片段配上艺术家对异化劳动充满诗意和哲理的反思。原始的负片已经散失,但经过数码修复的版本在这次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上首映,给观众带来了一次冥想的长长停顿。
9. 拉娜•费芙丽托(Lara Favaretto),《转瞬即逝的纪念碑》(Momentary Monument),(Galleria Civica,特兰托,意大利)
费芙丽托用三万六千个沙袋组成的临时装置将但丁塑像团团围住。这座落成于1896年的但丁像位于市区主广场,是特兰托1896年为抵御奥匈帝国侵袭,巩固自身意大利身份而建的。费芙丽托制造的幽灵(该作品参加的是由AndreaViliani策划,为标志Galleria Civica实验性新方向而举办的展览)让人想起街垒和一战,作为一种形式的撤离,以及作为争议场域的文化。由沙袋组成的墙壁很快就遭到破坏,部分垮塌了。
10. 皮埃尔•于热,未命名(Pierre Huyghe, not yet titled)(民间艺术博物馆,巴黎)
万圣节的时候我收到邀请,去一家最近关闭的民间文化博物馆里参加活动。这次活动是一个系列里的第一部分,因为暂时不知道如何处置这座几乎完全腾空的十一层建筑,所以安排了这个临时项目,该系列活动中的另外两次将分别于2010年的情人节和劳动节举行。观众-幽灵在楼里四处漫步,一群人扮演博物馆工作人员,包括保安、修复师、清洁工、馆长等。他们聚在另一群表演者的周围,看他们表演魔术、催眠、相声,重排八十年代法国恐怖组织“直接行动”(action directe)接受审判的过程。工作人员们就像参加某种庄严仪式时那样,入戏越来越深,最后简直要变成二度演员,成为他们所观看的表演者。观众成了“假观众”,演员表演着观看,但不知道整部戏向何处发展。回响和重复时有发生,角色的改变和转移暗示着一种病态,其根源在于如今这个图像污染严重的“资本主义”故事里,个体因为不断被复制而无法获得连贯一致的体验。整个过程中有兴奋,有快乐,有期待,有悲哀,还有最终平静的安宁。
卡洛琳•克里斯托夫-巴卡捷夫(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是2012年卡塞尔文献展艺术总监,意大利都灵凯斯泰勒当代美术馆(Castello Di Rivoli Museo D'Arte Contemporanea)首席策展人兼临时馆长。她同时还担任了2008年悉尼双年展的艺术总监。
文/ 卡洛琳•克里斯托夫-巴卡捷夫| 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
译/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