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纽约画廊重寻经典
今年,各种行业的市场都受到重创,但是纽约的画廊却以高质量的历史性展览予以顽抗,与本土的博物馆进行强烈竞争。有些很不错的大型展如高古轩的《曼佐尼:回顾展》和Speron Westwater的《纽约Zero》,但是还有一些更小规模的展览。L&M艺术推出了《约翰•张伯伦:早些年》(John Chamberlain: Early Years)和 《菲利普•加斯顿1954-58》(Philip Guston 1954-58), 也是对近来推崇艺术家晚期卡通式的创作的一个平衡,Mitchell-Innes & Nash将五六十年代被低估的阿兰•达堪基罗(Allan D’Arcangelo)和里昂•科索夫(Leon Kossoffs)推到众人面前, Paula Cooper则推出了大卫•诺夫(David Novro)的早期作品。Peternity Freeam选出了夏洛特•珀森斯科(Charlotte Posenenske)大量的金属模型,Skarstedt画廊则呈现了《芭芭拉•克鲁格前-数码》,给受到被窃取图像和光亮的数码效果束缚的一代,好好地上了一课。也许,其中任何一项展览都可以成为一个奇迹,但放在一起,它们则提醒我们,过度的丰富并非总是那么令人尴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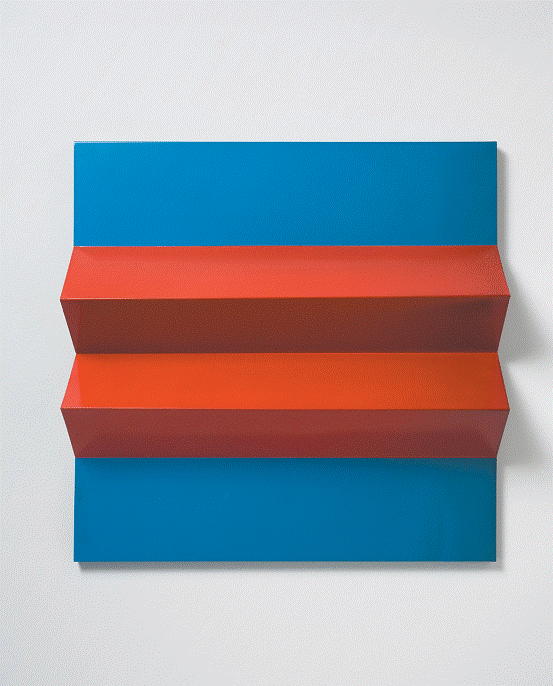
2. 杜尚(费城艺术馆)
杜尚迷人的Etant donnes (1946-66)被赋予了太多的诠释,但是,千言万语,不如亲眼去看看艺术家的准备性研究和相关材料,这样对他疯狂的创作过程才能有个最清晰的了解。坊间传言,在生命的后期,他公然放弃艺术而选择了围棋,孜孜不倦地研究了二十年。由麦克R。泰勒(Michael R.Taylor)组织的这场展览,将一位被以为已经抛弃实则却从未离开工作室和停下双手的艺术家,栩栩如生地带到了人们面前。
3. 查尔斯•雷 (Charles Ray)
对于雕塑家查尔斯•雷而言,今年是非常有成绩感的一年。首先,纽约的Matthew Marks画廊展出了八十年代三件不太被人注意却令人震撼的作品,其中包括《Ink Line》(1987),将雕塑的历史提炼成它本来的闪光形式。在威尼斯的Francois Pinault的Punta della Dogana,雷揭开了《拿青蛙的男孩》(2009),一个八英尺高的石膏男孩专注地盯着手中的青蛙,这只动物刻画得比手拿它的人还要细腻,这件作品迅速成为旅游者照相的最爱,大家站在这一敏感又单纯的纪念物,似乎并不觉得尴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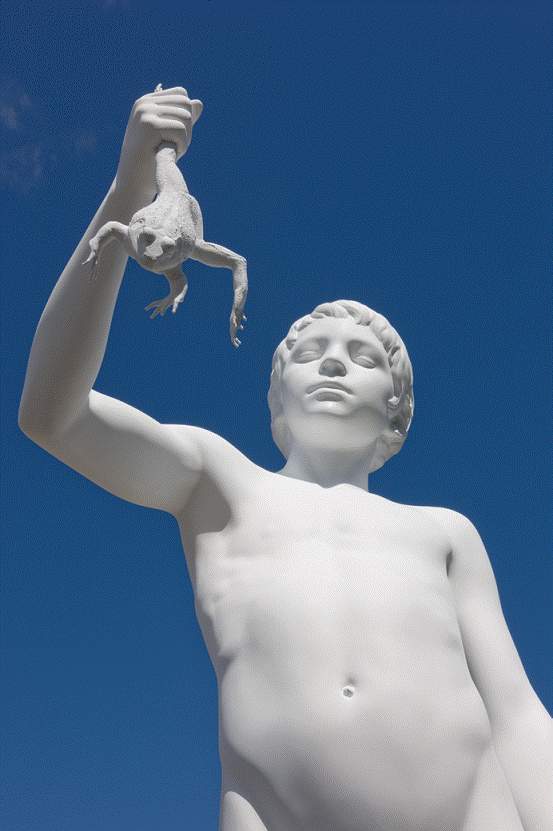
4. 艾瑞莎的帽子
如果说,查尔斯•雷的大尺寸青年像成为我心中年度雕塑的话,那么亚军将是艾瑞莎•富兰克林(Aretha Franklin)的BeDazzled的帽子,一个硕大无比、摇摇晃晃的玩意获得了新闻界的热情关注,富有善意的恶搞以及十万个facebook好友。虽然帽子有点盖过了她的脸庞,Aretha倍儿精神的头部装饰成为我们民族乐观主义和骄傲的一个至高点坐标。
5. 纽约舞蹈潮
就如本土画廊对过去做了精准的回顾一样,本地三家最优秀的舞蹈团再次复兴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艺术家和编舞者的合作。1979年特瑞莎•布朗(Trisha Brown)的劳森伯格设计的Glacial Decoy重回BAM,鲁辛达•却尔兹(Lucinda Childs)的《Dance》,在Bard学院和Joyce剧院重新上演。在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作曲的伴奏下,孩子们紧张而流畅的舞步在索尔•里维特(Sol Lewitt)的三十年前的电影幕布后转圈,偶尔不太连贯,却又令人迷炫。而Kitchen也重排了卡罗•阿米塔基(Karole Armitage)80年代著名的朋克芭蕾,查尔斯•阿特拉斯(Charles Atlas), 杰夫•昆斯(Jeff Koons)和大卫•萨利(David Salee)担纲舞美设计。
6. 纽约的希望
在这样比较动荡的时期里,也许唯恐人们多虑,感觉这个城市已被怀旧的伤感所笼罩,本土的三个颇有前途的艺术家遂以突破性的展览,在今年迅速成长起来。在瑞士学院,马洛•帕斯夸尔(Marlo Pascual)展出了旧货店的图片和其他的艺术品和食物,视角聪敏而独到。埃里克斯•哈巴德(Alex Hubbard),在Team放映了一些具有野心的录像,记录了摇晃的雕塑和零碎的拼贴画的制作与毁坏的过程。约什•布兰德(Josh Brand)在巴塞尔的艺术宣言和伦敦的哈罗德街展出了很多新的图片。他的小图片具有抽象摄影的美丽,对色彩充满喜爱,适度,优雅,机敏。

7. 彼得•多格(Peter Doig, Gavin Brown’s Enterprise和Michael Werner画廊,纽约)
在看到所谓的过渡期结束后,历史学家应该更了解什么是“过渡性的”作品。多格的双空间展中,人们发现,一位艺术家在达到高峰时主动选择了戛然而止,不再是那个我们所熟知的画家。人们很少看到这种改变,它们有时是美丽,有时充满挣扎,但一直在对油画进行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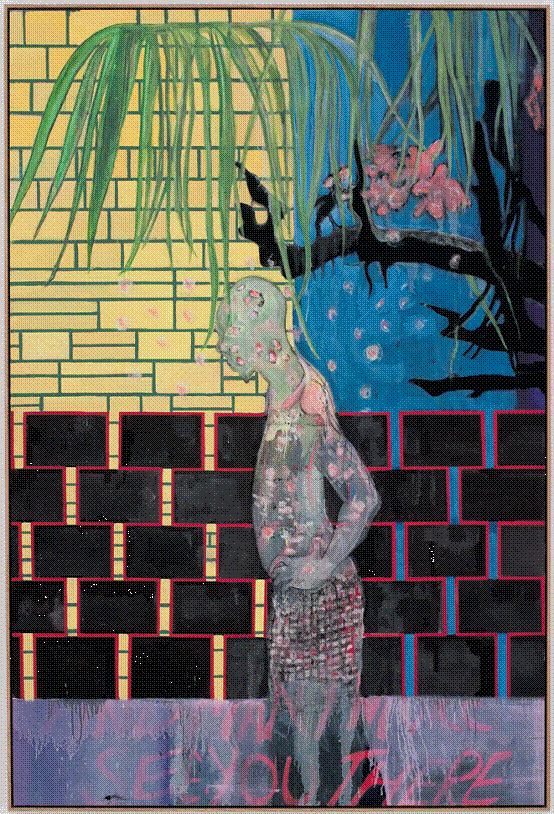
8. 约什•史密斯(Josh Smith, Luhring Augustine,纽约)
彼得•多格(Peter Doig)努力缩减他的绘画词汇,而约什•史密斯则正好相反,拼命地添加,多的都要爆了。他将数码摄影,计算机编辑,色彩打印,丝网印刷,大量的油脂都融汇在画中,这些画就好像在自我蹂躏,呕吐。鱼和树叶就好像画面的快速流动中的阵风一样,行家们试图将麦子从谷壳里剔出来,从而证明在整个搅拌过程中,所有的部分完全是必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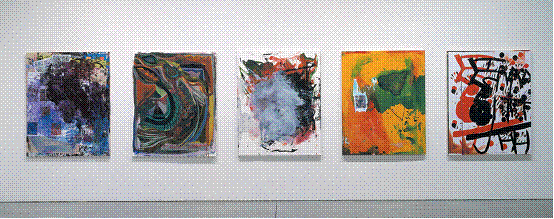
9.《城市中央:赫伯特•玛斯卡姆(Herbert Muschamp)精选》
对于那些认为建筑日益走高的人们而言,已故的赫伯特•玛斯卡姆既是启发者,又是捣乱者。在面对小官僚和粗俗的商业主义时,他对天才、伟大思想与另类新建筑的大力支持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都是无人可比的——就如这些引人入胜的文字中所散发出来的无穷魅力一样。
10. 琼•米罗:绘画与反绘画 (Joan Miró: Painting and Anti-Painting 1927-1937)
(MoMA,纽约)
米罗的野性力量似乎被他的海报和明信片作品的温情脉脉所融化。这场展览组织得很专业,策展人是安妮•昂兰德(Anne Umland),展览重新抓住了米罗流行文化样本中的粗俗气质和对于我们所称之为绘画的野蛮性攻击。
司各特•罗斯科普夫(Scott Rothkopf)是《Artforum》的高级编辑,也是一名艺术史学家,批评家。最新的著作为《杰夫•昆斯:画家》收录在《杰夫•昆斯:笨重的艾维斯》中。(Rizzoli, 2009)。
译/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