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从2005年起,我就担任了伊斯坦布尔文化和艺术基金的顾问,但此时还是无法避嫌,发自内心地认为,十一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可称得上是本年度最佳展览。艺术可以做什么,在这期的双年展充满了很多如此的可能性,所以在2009年的回顾中,首推这场大展。
“什么使人类着?”Zagreb的策展集体WHW(很么,如何与为谁)提出了这个问题,也是活动的标题。就如革命性的问题“有什么要做的”一样,其目的既有质疑性,又有辩证性。一方面,“什么使人类着?”这个问题暗示着:有时候我们对这个问题是多么得无能为力,《Territory 1995》 (2009)这样的作品,以及Hrair Sarkissian的叙利亚城市广场的摄影,都会令我们想起这样的困境。双年展的这些作品直接强调了题目中所提出的问题,反省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屡次地滥用生命的权利。这个问题源于布莱希特的一首歌《三分钱歌剧》,因为在艺术性的满足上,生命不仅仅是食物与简单的活着这样的问题。艺术在人类史上持续的存在证明着人们对自我意识的的要求,大家想去好好反思,人类存在的核心是什么,这是在我们现存的环境之外,人们共同的思考需求。同样,在想象性的思考中,艺术也不能忽视现状,否则只能沦为臆想。
通过提出布莱希特基本的问题作为一种展览的推测,WHW为一场展览奠定了基础,这场展览涉及了更为重要的问题,艺术在今日世界的作用,意即世界性的集体想象的状态。与当前进行的威尼斯双年展不同的是,后者认为,艺术与环境可以运用资源去产生一个无穷尽的双重世界,WHW的提议认可的则是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简单的推断,认为我们只有一个世界。策展人要求艺术家们去思考,艺术可以做什么,怎样与世间我们必须要做出的政治与经济选择并行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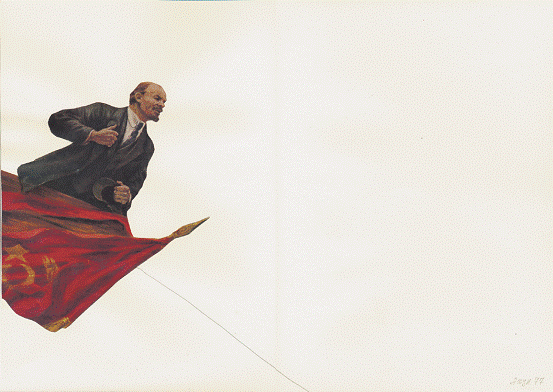
难道正是这一点使得2009年的伊斯坦布尔双年展成为了一场政治展,正如许多评论所要求的那样?问题的答案在于我们如何去理解政治,从何种角度去观察全球。展览绝不是一个激进主义展。它并没有冲向街头,也没有很多政治企图的艺术中所采取的那些介入社会的仪式。实际上,它运用了很多类似转喻性的美术,这些艺术存在于直接取自周围环境证明作品的自主性的那些设置精巧、类似博物馆的白立方中。双年展的政治并不是直接的干涉主义者,与马可•斯科蒂尼(Marco Scotini)在2005年开始的一直在进行的重要的《不服》(Disobedience)所记录的游行并不一样。
艺术中的政治表达在展览的过程中变得明确而实际起来,作为姿态,作为表达,对一个双年展而言几乎是独一无二的,通过创造一些反省的时刻,创作的语境被展现出来。在拉宾•穆若(Rabih Mroué)告解表演中,在沙隆•海耶(Sharon Hayes)不合时宜的爱的宣言中,在科维•库里克(Kwie Kulik)的孩子的幻灯片中,在阿迪•祖米耶夫斯基(Artur Z˙ mijewski)与波兰移民的访谈中,可以发现其中的政治姿态,这四件作品源于个人叙述的限制,对政治责任的发自内心的需求。通过将二十世纪意识形态战争高度的作品包括,艺术家探索了表现的形式,其中有维亚切斯拉夫•艾克胡诺夫(Vyacheslav Akhunov), 布莱莫(KP Brehmer), 山亚•伊维克维奇(Sanja Ivekovic), 穆罕默德•奥萨玛(Mohammed Ossama)的作品,以及姆拉登•斯蒂林诺维奇(Mladen Stilinovic)《无人想看到》(2009)这样简单而令人震惊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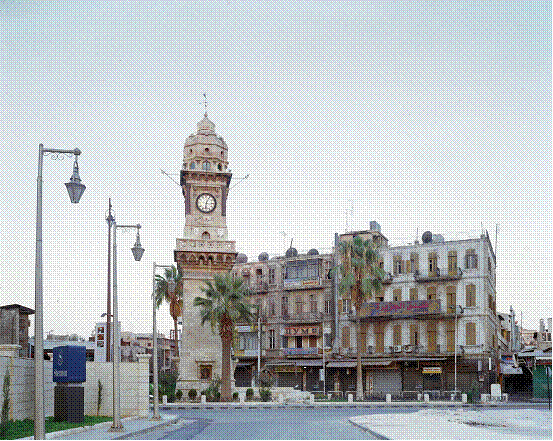
双年展探索的政治第三概念是最根本彻底的。对于展览劳动性的创造的反思方式在对无数个试试和数据的引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事实和数据关乎的都是金钱是如何被收集和传播的,艺术家爱在哪里出生,在哪里定居等,这种手法较明显地体现在Cengiz Çekil, MoAA, Aydan Murtezaog˘ lu和布兰特•桑加(Bülent S¸angar), Societe Realiste的作品中,它们都以政治序列与观看的动作相合并。
对于双年展政治策略的这个解释,令这个问题有了开放性答案:展览推动的是什么。这是理解的根本,因为艺术的政治可能性问题需要对于某种推动力进行表现:简言之,一场展览在观看和观看后的过程中,可以让观众做些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双年展非常准确地定义了艺术在教育方面的可能性:即政治动力—艺术作为教育性的干涉。来到双年展的观众可以学习,并为他们自己创作个人理解的新形式。学习的可能性有很多,从地理到文化,从美国到巴勒斯坦到荷兰,但是很明显,展览提出了现代主义的遗产的存在性问题,与之前所言的源于西方改造于东方并不相符。尤其是通过在中亚西亚的作品,双年展告诉人们,一场世界性的现代主义通过平行而竞争的世界关系已成长起来—-WHW通过将作品安排设置清晰地将这一信息表现出来。这个学习的过程与布莱希特的野心和被抛弃的唤起人们意识的左派理想相吻合。这场双年展,它的策展人和艺术家,坦然地表示,他们对当前世界上所存在的令人不悦的不平衡有话要说。他们认为,一场国际性的展览是表现这些情况的一种方式,甚至可以在情感上触动人们,因为他们在这种模式和它的草案方面,采取了非常独特的方式。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策展团队的努力和展现人们的愿望被实现的野心。展览是一场挑战,一把匕首,也许指向了这一领域的正中心,这个领域(或工业)理所当然地认为,艺术的意义通过经验上的交流产生出来,而这个交流是在平等的范畴下进行的,包括文化知识,政治权利,经济条件等方方面面,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语境被理解而没必要向外界做出明显的诠释。
在回顾中,展览感觉更像是一场公开的博弈。看完双年展后的感觉是很矛盾的,既有仰慕又有不确定感。艺术,艺术家,艺术产业,欲将泄露个中的秘密,改变其对自己领地的理解么?为了作为一种审美领地或一个特别的市场商品发挥作用,它有必要独处退后么?在开幕上反对双年展与这个国家最大的集团Koc Holding的合作的游行,也许是一切完全公开后,将会发生什么的一种预示。学院的自我批评打开了一盒蛀虫。
如果严肃地考虑一下,伊斯坦布尔所作出的努力赋予了一个集体项目极大的力量,再将艺术看成是想象的政治邂逅的一种方式,如果展览鼓励更多的机构想象出不同的方法,去表现语境,重新对教育模式进行改变,或者尝试一些更具干涉性的事情,那么,它的影响可能会巨大无比。在经济萧条中,也有迹象表明,越来越多的艺术和策展项目能够以更清楚的姿态去决定,当一件艺术作品为公共而做时,其边缘尺度应该是什么。十一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展现了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艺术和这种重要的主动精神,在国际上比以往更加清晰可见。
查尔斯•艾奇(Charles Esche)是荷兰Eindhoven的Van Abbemuseum总监,Afterall周刊的合作者。
译/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