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1919年与库尔特•施维特斯(Kurt Schwitters)相识之后,柏林达达主义者理查德•胡森贝克(Richard Huelsenbeck)对他有句十分著名的评价,他挖苦施维特斯是一个赖在“静止而舒适的中产阶级世界里”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下层阶级”——甚至还说他是“达达主义革命中的卡斯帕尔•达维德•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一个打着激进主义幌子的倒退者。施维特斯在美国的首次大型展览的确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个展览(由Isabel Schulz 和Josef Helfenstein策划)跨度将近三十年,最近在休斯顿的曼尼尔收藏美术馆(Menil Collection)拉开了帷幕。在1937年被流放至挪威之前,施维特斯一直都住在德国汉诺威,这也是他的出生地(并且他一直住在他父母的房子里),他一生都致力于创造最理想主义——并且表面上与政治无关——的艺术。正如他在1931年的宣言《我与我的目标》(Myself and My Aims)中所写的:“投入艺术创作就像宗教崇拜一样,它将人从日常生活的苦恼中解放出来。因此,艺术越是远离国家与社会等问题,越是关注单纯的人的问题就越能得到升华——(在审美体验中)全心投入,细心观察,直至忘我。”这似乎将他与胡森贝克等同时代的柏林艺术家区别开来。
然而,无论“国家和社会问题”与施维特斯的艺术创作相去多远,国家和社会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流通、交流的结构,以及构成前者的众多元素的集合——都是其艺术实践的核心。施维特斯游移于审美理想主义与社会批判之间的这种机巧和灵敏使他的作品具有重要意义,在今天,我们自己的国家话语也游移于保守倒退与大声疾呼之间,普遍存在的经济与政治危机再一次使最落后的那种僵化的文化死灰复燃。
施维特斯将自己的集合艺术统称为“默茨”(Merz),这个词是他去掉德语单词Kommerz(“商业”之意)的第一个音节而自创的,它本身的拼写只是一个银行名称的一部分,令人想到Commerz-und Privat-Bank(德国商业银行)。施维特斯自1919年开始创作“默茨”,那年魏玛共和国刚刚成立,到处是动乱与革命——而对于施维特斯来说,那却是在艺术创新方面充满了无数可能性与必要性的一年,他采用了一种变形的交易语言,这预示着他新的艺术计划。以“默茨”为名,他以印刷、设计、表演、装置、诗歌、散文(文学散文与批评散文)等多种方式进行创作——更不必说拼贴、集合、绘画和雕塑了。他在1923年公开宣告他的“默茨”绘画的产生,这种绘画的功能就是研究一种“集体世界的形式,一种宏大风格”,我们从在曼尼尔举办的这次展览就可以窥见这一主张。本次展览展出了施维特斯的一百余件作品,包括拼贴、集合、浮雕和雕塑,数量之大,种类之多,令人叹为观止。此外,本次展览还包括Peter Bissegger首次在美国对《梅兹堡》(Merzbau)的部分复原,《梅兹堡》是一个由木材、石膏和精心挑选的碎石块构成的一个房间,施维特斯耗费了十余年时间才创作完成,但它在1943年毁于联盟国军的轰炸。如果施维特斯是支持Gesamtkunstwerk或者说总体艺术的关键人物,那么所有这些努力则共同展示了他力图完成这项计划时所使用的方法的绝对精确性:在他的浮雕与集合作品中凸起的每一块涂有颜色的木头,在他的拼贴作品中的每一层纸和布,都变成了他每件作品中所创造的那个私密世界中的最基本元素,同时也是它们所共同构造的那种总体化面貌的基本元素。对于施维特斯来说,Gesamtkunstwerk永远都是一群重新组合在一起的片段,是从一个整体中分离出来的不同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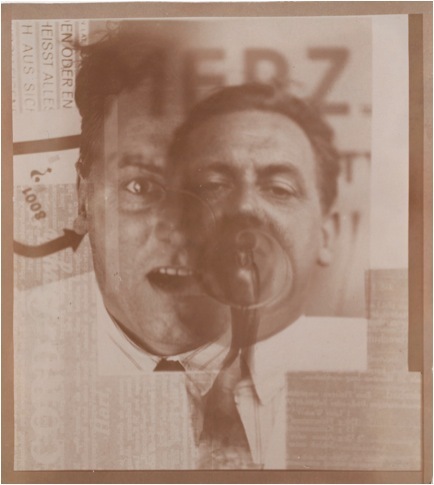
施维特斯将“默茨”理解为一种均等化的动态过程。正如他在1919年所写到的:“从本质上来讲,‘默茨’这一术语意味着将所有可以想象到的用于艺术创作的材料结合起来,并且以技术的方式对其予以同等的重视。”如果说曼尼尔展览上的作品呈现出各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主要是拼贴作为一种绘画活动,从主导20世纪20年代早期作品的由那种圆形和矢量构成的严谨形式,经过20年代中期所大量出现的简洁的几何构成,转变为流放挪威期间所创造的一种日益开放的场域与更加鲜明的具象形式——那么将这些不同视为一种连贯有序的形式发展就错了。施维特斯从他所碰到的几乎所有事物中选取材料,从柏林达达到国际构成主义,而且在其整个艺术生涯中,各种各样的形式经过最后的组合后,都能够相互重叠映衬。我们并不应该感到奇怪,施维特斯,作为一个现代抽象艺术的先锋,从未完全放弃他年轻时的具象绘画:他仍然坚持画肖像和风景,并且没有任何嘲讽之意,直至生命终结。
施维特斯的拼贴作品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材料,更在于其实验性。虽然施维特斯从未涉足摄影,但其拼贴作品却始终有所指向,这些粘合在一起的团状物构成了层次丰富且极为详细的指向,它们记录着1948年他在英国安布尔赛德逝世前的喧嚣纷扰的三十年里的各种活动与旅行。这在那些不断变换的文字片段中显得尤为明显——商品的包装纸、报纸碎片、行李寄存处的存根,等等——它们布满了作品的表面。从德国到荷兰,从挪威到英国,这些作品体现了他漂泊而健谈的一生,最终以流放的十年结束。施维特斯反复声明,他的材料丧失了他所说的Eigengift(self-poison一种特殊的毒药),不能将拼贴结构的形式组构连接在一起。但是,曼尼尔展览却证实了他真正所关心的东西,即构成其作品的每一个碎片的来源。巧克力包装纸和电车车票出现得尤其频繁,这表明他关注交通及身体内部的循环,它们与拼贴本身的循环结构相对应。“默茨”(Merz)一词来自“商业”(Kommerz)这并非偶然——因为“默茨”表现的主要是交流、迁移和流通,这在所有经过重新思考并改进的作品中都可见到。正如艺术史家罗杰•卡迪纳尔(Roger Cardinal)所说,施维特斯的拼贴“有微型地图的特点,或者说……它们都可以被比作垃圾坑,对于关注一个失落社会的物质文化的考古学家来说,它们传达着一种日常生活的叙事。”

经济学的修辞也给施维特斯的大量文学作品带来了生机,不仅是《诗歌25[元素]》(Poem25[elemental])等作品,他在1922年创作的抒情诗也完全由数字和比率组成(例如它开头便是“25/25,25,26/26,26,27”)。1919年的诗歌《致安娜•布鲁姆》(An Anna Blume)可以说是施维特斯最著名的文学作品,它将每个句子里的词语,每个词语里的字母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其最基本的关注点,打破语法与语义规则,令人想起富有表现主义色彩的浪漫主义诗歌的修辞学,也让人想起消费市场与价格大战的修辞方法。遍布丑闻的市场推广活动使这首诗在德国变成了一种流行的讽刺形式,它颂扬了一个女英雄,她有一个特点就是她的名字是一种回文倒序。这首诗写道:“一个人从你的背后也能读懂你/而你,最辉煌的你,/你前后一致:/A-N-N-A。”就像一个名字的两半,《致安娜•布鲁姆》半开放半封闭的语句相互映衬,每句话都在宣布:“leb liebe Dir!”——施维特斯将其翻译成英语就是“我爱你的一切!”但是更确切的说,应该翻译成“我爱致你(I love to you)!”——由此,浪漫的诗句发生了语法的错误,爱的焦急渴盼也与语言的任意规则对立起来。施维特斯1920年代晚期的众多艺术方案之中,有一种是对德国字母表本身的修正,他试图去创造一套发音更准确的字母——正如他在论述书写的一般作用所写的那样——书写是“写就的语言与声音的图画。”施维特斯的目标(当然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不仅仅是对语言文字排版的再设计,而是对字词与结构的完全重组——更进一步说,是对其中所引发的思想的重组。正如他在1927年开始写作的一篇文章中所介绍的那样,“一部系统的手稿其实只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复合体的一个元素,这个复合体中包括系统的语言与系统的思想。”
在整个1920年代,施维特斯本人也一直处于不断辗转中,他与各种各样的人物旅行和合作,这其中有赫尔瓦特•瓦尔登(Herwarth Walden)、埃尔•利西茨基(El Lissitzky)、拉乌尔•豪森曼(Raoul Hausmann)和凡•杜斯堡(Theo van Doesburg)——并且,他和这些人的联系还说明他的艺术创作游移于表现主义、达达和构成主义之间。汉诺威地处边缘,以中产阶级财产的堡垒而著称,它不仅是施维特斯的艺术源泉,也为其提供了材料:由于居住在这一边缘城市,他强烈感觉到自己不能不与欧洲的前卫艺术进行合作和联系,即使他将汉诺威作为他文章里的主角,他完成了市政建筑的设计工作,并且明白他自己的名誉是与这座城市息息相关的(这里必须要说的是,在汉诺威,还有一些人和机构——例如博物馆馆长Alexander Dorner和新建的具有前瞻性的当代艺术展览空间Kestnergesellschaft——构成了一个比较小但是很活跃的前卫艺术圈子)。有了词汇、风格和拼贴用的材料,施维特斯将中心与边缘之间的联系——或者更确切的说,他将形成这些联系的文化观点与实践——作为他的基本素材。
施维特斯在1923年至1932年之间(与利西茨基等人一起)以多样的形式创立的一本影响深远的前卫艺术杂志《默茨》,就是这些努力的最佳证明。然而,他对于批评者的辛辣回应与他无数次的公开演讲一样引人注目,他将这些批评者称为“Trans”,他的这些言论在《默茨》等20年代的报刊杂志上广泛登载。施维特斯认为,拼贴与艺术领域的奋斗一样,对于二者,他投入了同样的心血,也获得了同样的快慰,他以独特的视角将观念的“Eigengift”聚集起来,将其完全转变为另外一种东西。他与达达主义之间不稳定的关系在这一语境下显得尤其有意义。胡森贝克拒绝了施维特斯,施维特斯不断反抗胡森贝克,这使得施维特斯一直都是柏林达达另一些核心成员如汉娜•霍克(Hannah Hoch)和豪森曼的亲密朋友;正是因为1919年他的诗集《安娜•布鲁姆》的封面上打上了DADA的标志,所以在第二年他给平版印刷版的《大教堂》(Die Kathedrale)的封面上贴了一个恰恰相反的标志——CAUTION: ANTI-DADA(注意:反达达)。

大教堂的形象被施维特斯反复使用,这在他的《梅兹堡》中尤为明显。《梅兹堡》的核心部分——一个巨大的可移动的圆柱体,他在1920年代早期就开始制作它了,在这个圆柱体上有许多洞穴,里面充满了媒体的碎片和个人的纪念物——他将其称为“the Kathedrale des erotiscben Elends”或者“色欲痛苦的教堂”。所以,由曼尼尔校园来主持Bissegger在美国本土上对《梅兹堡》的首次复原就再合适不过了,因为这里是罗斯科小礼拜堂与拜占庭壁画礼拜堂博物馆的故乡。这一装置是在1980年代依照原作结构的有限的照片记录而完成的,它能帮助我们推测和想象《梅兹堡》原作在1943年被毁前的样子,它安装有彩色的灯,并且可以看到汉诺威的施维特斯工作室旁边的那个树木茂盛的公园,不过这个景象是假造的。当然,这个装置缺少了原作的许多特殊材料:特殊的气味和表面质地,施维特斯从朋友那儿偷来并钉在墙上的一些私人物品(包括Hans Richter的一缕头发和Sophie Taeuber-Arp胸罩),一杯艺术家本人的尿液,据说他将尿液照亮来模仿液态的黄金。Bissegger所做的一切复原工作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施维特斯这件最伟大的作品,并且它无疑也征服了原作,它干净的墙壁和明确的博物馆功能与本杰明•布赫洛(Benjamin H. D. Buchloh)对《梅兹堡》的描绘截然相反,后者认为《梅兹堡》“完全没有任何效用,绝对有功能障碍,(而且)完全拒绝将空间体验诉诸合理性、透明性和制度化。”
正如它的材料形式一样,《梅兹堡》创造的具体日期一直以来都没有定论。最近的研究更倾向于将其定为20世纪30年代早期,而非以往所认为的20年代中期,因此施维特斯早年的圆柱计划被理解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和建设(曼尼尔将这件作品的创作日期大致定为1923至1936年,所以包括了之前的这些作品)。这五年的推后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就不仅将《梅兹堡》看作施维特斯拼贴艺术中的一个圆柱体,或者是一个受表现主义影响的装置实验(就像它最常被认为的那样),更将其视为对于魏玛德国晚期正在消逝和崩塌的民主政治与前卫文化的一种特殊回应。《梅兹堡》是一个可居住的并且不断变异的记忆宝库——一个圣物匣——它诞生于一个正在崩塌的世界。
就在被流放之前,施维特斯还在拼命争取到在美国建造《梅兹堡》的机会。虽然1935年Alfred H. Ban Jr.在汉诺威拜访了他,收藏家Katherine Dreier自20年代就开始和他通信来往,并支持他,艺术家的愿望还是没能实现。1937年,施维特斯逃亡挪威,三年后又来到英格兰,他在两地都曾实施过《梅兹堡》的创作,但是因为战争和疾病的折磨,两次都没能完成。尽管这些作品几乎消失殆尽,施维特斯的重要地位却被保留了下来,对于战后时期的美国艺术家来说尤为如此。曼尼尔的这件装置正是在其最后展出的美术馆里对这一历史的认可,这里有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贾斯伯•约翰斯(Jasper Johns),罗伯特•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tg)和塞•通布利(Cy Twombly)的作品,它们与精选出来的施维特斯最后一年创作的拼贴作品一起展出。的确,施维特斯的艺术实践依然深深影响着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在2007年,纽约博物馆选择在纽约包厘街以多单元展览“非纪念碑” (Untnonumental)的方式举行开馆仪式,当时还有哪个历史人物能比施维特斯更能引起共鸣?从Thomas Hirschhorn 到Rachel Harrison,再从John Bock 到Gedi Sibony,施维特斯周旋在浪费与补偿,形式与指示,材料特性与系统分析之间,这在当代艺术实践中依然能引起强烈共鸣。施维特斯最令人感佩的遗产是他在创造和审视事件、身体、信息之类事物——从图片到诗歌,从报刊到字母表——的流通结构时所具有的强度与深度,以及他触及但从不完全屈从于预定的政治经济秩序的奋斗方式。

令人惊讶的是,其实政治也出现在施维特斯发表的文章里,但总是间接地与他的艺术实践相联系。例如,他1924年的文章《民族感情》(The Feeling of Nationality)描述了德国这个国家从四分五裂的几个部分变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一过程强烈地启发了他自己的拼贴创作,“最终,生活在一起的人们以国家的名义聚集在一起,这有很多偶然的成分。”这一句话至今仍显得意义重大——而对于很多人来说,则显得异常危险。因为正是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时代,全球的人流、信息流和物流空前流动,强硬分子们对于不可逾越的界限和绝对不变的身份的渴求到达了白热化程度,就如同金本位制本身——金本位!——又重新盛行一样。当然,这对于施维特斯来说会是一个熟悉的领域——我们的问题与1920年代德国的问题不能相提并论——而且它有助于解释他作品中不竭的力量。“默茨”的收集与集合计划,以及对于几乎所有事物的细节及其广阔内涵的密切关注,将分离与统一放到了艺术实践的核心位置,将社会的材料、结构和程序作为艺术创作的素材。这正是施维特斯作品的精髓,而这也正是以后世世代代的艺术家们所努力追求的:创作与生活无关却来源于生活的艺术。施维特斯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里;他对这个世界所作出的回应就是收集和组合碎片,并以此重新思考整体的概念。
“库尔特•施维特斯:色彩与拼贴”目前在休斯顿曼尼尔收藏美术馆展出(至1月30日);3月26日至6月26日将巡展至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8月3日至11月27日将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艺术博物馆展出。
格拉汉姆•巴德(Graham Bader)的《镜厅:1960年代罗伊•利希滕斯坦和绘画的面孔》(Hall of Mirrors:Roy Lichtenstein and the Face of Painting in the 1960s)去年由MIT出版社出版。
译/ 梁舒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