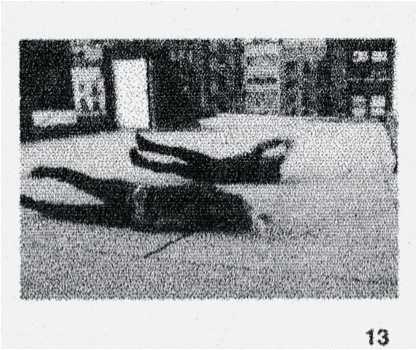
2000年六月初,我第一次去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当时的我很天真,也就是说博览会先让我感到震惊,然后是万分沮丧。整个大厅里全是画廊摊位,很多摊位上摆着我熟知并且喜欢的作品(皮耶罗•曼佐尼和马塞尔•布达埃尔),还有我远远仰慕的艺术家的作品(杰夫•沃尔和罗德尼• 格雷厄姆),以及具有历史价值的经典之作(彼埃•蒙德里安和埃德-拉斯查)。另外一些作品出自我认识的艺术家之手。眼前一切让我猛然醒悟的同时也生出一股凉凉的悲哀;当我回到在“商务酒店”(不带任何讽刺意味)的住地时,发现自己同样不带任何讽刺意味而且非常老式地心碎了。因为对我来说,到目前为止,这些艺术品不仅仅意味着一堆名字,还代表着观念的集合体,其内部交流主要发生在书籍和杂志上,在酒吧深夜的讨论中,并越来越多地(以一种令人深感兴奋的方式)出现在展览空间内。看到这些观念被挂在博览会墙上随时待售的样子实在叫人难受。第二天,我回到展场去接受这种新式艺术观看形式的再度冲击,中途碰到一个认识的艺术家。她是少数亲临现场的艺术家之一。她说她刚到,我立刻警告她要小心入内。这可不是艺术家待的地方。
毋庸置疑,过去十年发生了许多变化。艺术博览会经历了自己的神化过程。它们的影响力堪与著名的大型群展相媲美,有时甚至赶超后者;而另一方面,现在很多展览无论从外观还是感觉上都让人联想到挤挤挨挨的博览会,高密度摆放的作品让寻找新事物的刺激和速度盖过了形成共识的慢节奏。但最大的变化还是艺术家在这个新图景内扮演的角色。新环境不再期待(或允许?)他们置身事外。相反,这些博览会越来越依赖于艺术家在场,主办方邀请他们为博览会量身定制“特别项目”,或以讲座和研讨会为名展示他们的观点。对许多艺术家而言,博览会已经和美术馆展览一样具备可行性和合法性。虽然这一点让我感觉不舒服,我却不能随便下判断。艺术家也是工作者,而雇佣环境已经今非昔比。老爸有退休金,我没有。糗事到处有。资本主义一统天下。
几年后,我参加另一个博览会时,在笔记本上草草写下了“克拉拉•利登/Reena Spaulings”几个字。但因为不善记录,我没有记是在哪个博览会上看到的这件作品,也没有记作品名。最近翻看笔记本时偶然发现利登的名字,当时是用铅笔写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也足够让我回忆起对这件作品的第一印象—“可爱的萝莉女战士挥着一根钢管把她的自行车砸了个稀巴烂。”这段低技术含量的短小视频《社会躯体》(2006)似乎对皮皮洛蒂•瑞斯特“女孩儿砸汽车”的录像《Ever Is Over All》(1997)在二十一世纪的回应。与后者的欢乐气氛相反,《社会躯体》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行为发生在空荡的室内,而不是户外;利登破坏自行车也不像瑞斯特录像所展示的那般随意,而是非常精准,经过了严格控制。她首先是试探,以几乎怜爱的态度轻轻敲击自行车;然后下手越来越重,一点一点地把自行车砸得七零八落。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段录像是一件情色佳作—是关于推论、推迟和延缓满足的s/m写意。利登和瑞斯特在破坏行为上的另一处明显差异是利登让我们感觉她正在毁坏的是自己的财产,而非他人之物,这样做无疑等于为她本人的日常生活又增添了一点难度。

在博览会上看到利登砸自行车非常过瘾。砸这个动作明显受到朋克毁坏乐器的启发,但录像还暗示着财产和使用价值之间极度暧昧的关系。如果瑞斯特的录像赞扬了九十年代女性主义朋克运动“暴女”(Riot Grrrl)的兴盛,并可以被回溯性地视为后者最终商业化的一部分,那么利登的录像就代表了后性别、后批判艺术家无声、甚至自闭的感知力,也许这就是我们时代的面孔。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犯罪的浪漫,也不是能把愤怒变成欣喜的幻想;此类救赎绝不在今天的想象范围内。相反,工作中的艺术家是沉默的、阴郁的、孤独的,甚至很有可能是自我否定的。
利登的作品看得越多,我越被其中的气质和效果吸引。在2003年的录像《麻痹》中,利登在瑞典的火车上表演了一出狂野奔放的舞蹈,试图挤进行李架或者在座位之间飘来荡去的艺术家让同行乘客经受了一场小小的惊吓。2009年,她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一间小展厅里搭建了一个巨大的白色立方体,占据展厅大部分空间,只在周边留下狭窄的通道。立方体上小心翼翼地放着手脚架、焦油纸和大捆大捆待回收的废旧纸板,本来毫无用处的立方体瞬间变成一个巨大的基座。整件作品令人捧腹:白立方成了名副其实的白立方,并被用来安放一座完全由垃圾做成的“雕塑”。接受吧,Moma!但利登显然很清楚,作品仍然受到展厅的限制,甚至是界定。她没有像乌尔斯•费舍尔或凯特•吉尔摩那样在墙上打出大洞;她只是在现代主义的白宫内再玩儿了一把基座和垃圾主题——曼佐尼还有阿曼。
上述三件作品都带有一种高中生式的叛逆:砸自行车,在地铁里装疯,冲最大的美术馆竖中指但又接受其限制。就此而言,这些作品共同贯穿着一种深刻的、几乎受到压抑的身体上的绝望感。事物被划定界线,被折叠,被捆绑,或者向前推进,濒临暴力的边缘——一边是外部局限和《麻痹》这类题目所暗示的静止状态,一边是接踵而至的狂野行为,作品在两极之间来回滑动。但利登的作品绝不是简单的情绪发泄,原因就在于前者深知并间接指涉了现代雕塑和舞蹈的历史、早期电影以及构成具体在地性的各类实践。愤怒受到了严密的控制和精确的升华,所以在她的作品面前,你不会感到恼怒(类似面对调皮小孩儿的父母的恼怒),只会觉得感同身受(“哥们儿,我明白你的感受,但你也知道,有些事情就这样,日子还得好好过下去”)。

就是因为这些作品,去年我推荐利登参加了圣安东尼奥的驻留项目。她在那里展出了两件作品。在其中一部很短的录像里,我们看到艺术家坐在一张光秃秃的桌子前,背对观众,拍摄地点估计是她的工作室。画面最初没什么动静,直到利登起身,然后开始非常故意地要把自己塞进旁边的垃圾筒里,仿佛她的身体不过是一个废纸团。这件作品引人发笑。也许是为了削弱过分的情感诉求,利登选择了本地百思买(电器商场)里最不起眼的一款电视机来播放这段录像。同时,她在楼上用焦油纸制作了一个复杂的装置,里面装有三部录像的投影。每部录像的内容都是利登在完成一个毫无意义但又十分艰巨的体力活动。在其中一面墙的投影中,她正从一根户外的水泥柱上往下爬。我们只能看到她紧紧抱住柱子的腿和手臂,她的头部距离地面足有六米多。另一面墙上,她站在一个看起来像是废弃停车场的地方。时间是深夜。她的身体缓慢地前后晃动,然后以一个运动员似的标准空翻动作狠狠落在柏油地面上,再一跃而起。这套作品完成于2010年,题目叫《群舞者》,意指那些芭蕾舞团里技术过硬但又不是舞团明星的群舞演员——他们的任务就是充当背景,填满舞台,让领舞的明星更加星光闪耀。
如果说在我之前看过的三件作品里,幽默还只是隐藏的痕迹,那么在圣安东尼奥展出的作品就充分显露了她的喜剧天赋,从某种程度上让我想起巴斯特•基顿的默片以及亨利•伯格森的重要文本《笑》。基顿的作品常常被解读为象征着男性气质在二十世纪初表征中的危机。他的人物形象塑造主要围绕矮小的身材和从不在摄像机前露出笑容的“冷面”展开。片中,他总是处在这样或那样的身体困境里,而好莱坞经典的时间凝固效果不仅让观众产生一种身体上的紧张感,同时也对男性气质编码进行了精确定位。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出版很久以前,基顿就已经揭示出所谓男性气质其实是由一系列对外部刺激做出的规约性反应组成,这些反应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失败的部分就是伯格森论述的重点。伯格森在《笑》中写道,事物失灵或运转不良会让人感觉好笑。这就是滑稽剧的语言,而基顿哀伤的幽默就建立在设备或身体的运转故障之上。但我觉得此处的“故障”还应包括基顿试图遵守男性气质规范过程中的失败,或更准确地说,是适应中介身份的失败;通过这种失败,他让我们看到了男性气质本身的建构属性。

把利登放到基顿开创的“传统”下讨论会很有意思。那么,此处展示的失败或失灵到底是什么?利登的作品技术含量很低,所以机械故障在她录像里的作用绝不像在传统滑稽剧中那般重要。虽然她富有爆发力的行为表演的确受到机械或技术(火车、工业产品、电影和录像动态结构)的阻挡和限制,而且也的确与后者形成了某种对话,但失败作为行动不顺或事情砸锅的代名词,却只触及了问题的一部分。无意义才是核心所在。这种无意义被表述为当代生活,特别是文化生产的普遍状态。关键不是自行车运转失灵,而是自行车只应有一个有效功能的观念遭到了严重质疑。
这种失败/无意义的纽结也出现在利登2009年的录像《Kasta Macka》里(瑞典语,字面翻译为“扔三明治”,俗语意为“打水漂”)。录像共分三屏,三个屏幕显示利登站在三条不同的河边打水漂。但童年的游戏很快变了味道,利登往河里扔的东西越来越大,动作几乎带着一种绝望,徒劳地想把所有被冲上岸的东西放回水中最后的安息地。在《Ohyra》(2007)中,我们看到她置身于一个肮脏拥挤的厨房,面对镜头数落自己哪些事没做(看望祖母),哪些事没做好(洗盘子,少对女孩子胡思乱想)。她头戴一顶老式皮帽,一边自责一边击打自己的脑袋。她在生活布置给她的一些基本任务上失败了,但看着这段录像,我们忍不住想:就算她成功了⋯⋯又如何呢?在这些地方的“成功”又意味着什么呢?对于利登来说,徒劳的行动和有生产力的行动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各种细小失败累积起来就让我们看到了如今新生代艺术家的核心困局:首先,当一名艺术家本身就是一件徒劳的事。
利登在作品中戏耍的另一种失灵体现在她本人无法被传统的性别区分归类上。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一直对使用“她”来指代利登感到犹豫,因为利登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典型的妇女或女性特质。同时,当她娇小有力的身躯穿着牛仔裤、无袖上装、套头衫在城市穿行时,我们又感觉不到任何男性气息。但残酷的性别二元划分仍然像幽灵一样在作品中徘徊不去。利登2008年国际妇女节当天拍摄的一张照片充分说明了这种复杂性。照片上的两个人扭打在地上,展览画册的说明告诉我们,其中一个人就是利登,但我们无从证实,光看照片上也不能分辨两人的真实性别。因为在利登的作品里,制作过程中的身体活动和消耗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在描述她的创作实践时,我感觉如果回避性别语法的问题就会说不下去。这种语塞不仅限于我的批评工作;作品本身浓缩而粗暴的身体性也使其显得沉默。的确,这里的沉默在几个层面上起作用,既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情感表达。口头语言明显缺席,加上后朋克音轨低沉的蜂鸣声,给人一种刻意或强制的沉默感。除此以外,性别的语言学要务又似乎要榨出身体与身体、行动与行动之间的差异。正如声音被消除,即使带有侵略性力量的身体也没被按照典型的艺术家在场方式处理——也就是说,所有身体行动都经过了中介(录像也好,照片也好)。中介和无声相结合并不是为了跳出语言或表征之外(作品根本没有给你留下任何“外部”的想象);她的目的可能是,(只是可能而已)找到一种方法,保持超前一步。


对于利登来说,到目前为止,保持超前一步意味着两件事:藏起来或控制录像播放的空间。在2007年的作品《无题(后室)》中,她在一个博览会的摊位(后来搬到一家画廊展览)建造了一个一次只能容纳几个人的房间。密道的门就藏在墙上的一幅“画”背后。“画”是用足足10英吋厚的旧海报粘在一起组成的,海报是利登从街头广告牌里裁下来的,最上面一张海报被刷上白漆,只能看到五颜六色的边缘。《Hus AB(House Inc.)》(2003)是位于德国斯普雷河岸边的一间小小地下室,空间仅能容两人居住,路人从外面完全看不出来。
这些结构以及其他一些针对画廊空间的临时改造常常用到对接管道和预制墙板,所以很多人把利登的作品放在建筑学框架内讨论(她进入艺术院校学习之前的确学的是建筑)。虽然我们无法否认她的创作里存在着建筑学冲动,但我本人对于利登究竟是空间的制造者还是破坏者这类问题并无太大兴趣。对我来说,与其把那些封闭或填满的房间和秘密通道看作她对建筑以及建筑学体系的批判,不如将其视为她阻断性别语法的同构异形体。八十二年前,伍尔夫第一次把对“一个人的房间”的需要摆在公众面前,如今,利登这些隐蔽的小屋和奇特的构造是否提示着在当代,“一个人的房间”可能是何模样?

如果是,那么利登似乎在暗示,它可能不是一个收入来源稳定的独立场所。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时代,性别和阶级划分是透明的,而且完全以从上至下的方式维持。但在如今我们身处的社会,这些类别的管理划分同场以隐蔽的方式进行,而且总是非常灵活。如果想在这场游戏里领先一步,艺术家也必须保持敏捷。
利登从未停止移动;她不断回收重构自己的作品,方法之一就是为录像放映制作新的背景。在《诡异的操纵》(Unheimlich Manöver,2007)中,她仔细地把自己斯德哥尔摩公寓里所有东西密密麻麻堆成雕塑的形式,放到展厅中央,录像则装在雕塑内部或周围播放。她在其他很多地方复制过这一装置,并经常变换播放的录像内容。
最近,她在伦敦蛇形画廊举办个展,该展览将于今年五月移到斯德哥尔摩现代美术馆继续展出。在这次展览上,她大大改变了最初在Artpace作为整体环境一部分的录像内容。爬水泥柱和把自己塞进工作室垃圾筒的录像被装进新作品《总是在别处》(2010)。该作品由两部分构成(首展是在巴黎的Jeu de Paume)。首先是一间从地板到天花板被折叠的广告海报塞得满满当当的房间,观众根本不可能入内。这些填充物又与同场展出的海报“画”形成呼应。临近的一间展厅内,三部幻灯机不断闪放着模糊不清的大幅黑白图片,画面内容几乎无法辨认。慢慢地,随着你逐步适应投影的节奏和图像格式,你就会发现屏幕上播放的是定格照片,或者准确地说,你可以隐约辨认出地面上的人影,也就是一块颜色稍微浓重些的墨点(让我们面对现实吧,给墨点分配性别是不合情理的)。三个屏幕分别显示她把自己塞进垃圾筒,爬水泥柱,以及把自行车骑进塞纳河的全过程。为了取得这种粗颗粒、低像素的图像效果,利登首先对录像截图拍照,然后高倍率放大照片,再把得到的图像翻印到醋酸纤维板上,最后做成家用幻灯片。投影仪咔嗒咔嗒的换片声为录像增添了时间的节拍感,中和了原来令人捧腹的喜剧色彩。当然,录像仍然很好笑,只不过从捧腹变成“偷笑”。而作品制作的媒介更加重了这种克制感——2009年,柯达宣布停止生产富有传奇色彩的柯达幻灯片,而利登此处又用自己的方法复活了这种实际已经不存在的材料。低科技是一回事儿,通过DIY重塑曾经的低端技术又是另一回事儿,后者让作品变成某种数字时代的滑稽剧。

《总是在别处》里的时间性无处不在——废弃的广告牌、过去行为的记录、“死而复生”的幻灯片。换句话说,尽管题目暗示了一种地点上的持续位移(全球游牧艺术工作者,永远在路上),作品本身也无法完全以一种时间或空间的方式呈现。(那种“你必须在场”的行为表演或重演,我们已经看得够多了)。利登再度分解了艺术生产和流通框架,在其网络中引入与功能性如此复杂的关系,如果这件作品下次以完全不可见的形式展出,我也毫不惊讶。
我在看利登在蛇形的展览时,就已经对她作品中内在的沉默质地深感着迷。一个朋友跟我讨论时提到了罗兰•巴特的生前倒数第二场讲座“中性”。巴特认为,中性是破坏西方文明内在二元对立逻辑的第三种元素。“众所周知,言语,言语的实施,与权力问题紧密相关,”他写道,因此“中性=提出沉默的权利——一种保持沉默的可能性。”读到这里,我感到很高兴。我想,我应该就此永远闭嘴。只有这样,才能“逃出”目前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困境:每个人都变成了消费者,用美元“投票”,多数人都无法依照自己内心的道德准则生活(那些挡不住的中国进口商品、常旅客里程积分、手机电池、滥用的毒品)。但是,任何把沉默当作“立场”依赖的态度同样不可取。正如巴特所言,这样的沉默“将自身浓缩为一个符号(也就是说困在了一种范式里):因此,中性意味着避开范式,最后必将非常矛盾地尝试超越沉默。” 这就是重点所在;把沉默当成一种策略意味着承担使其陷入流俗的风险。这一点让我想通了利登为什么总在改变作品的形态。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追求新颖,而是对避免凝固为单一形象的又一次(徒劳的)尝试,是为了避免成功运用艺术当前的流通模式:艺术博览会,三十岁艺术家的中期回顾展,无休无止的驻留项目⋯⋯所有这些出现在她履历上的事件都标志着她越来越成功,越来越合法。她努力使自己不落入其中任何一个流通渠道,以此尝试(并未能?)超越体系的凝固。

我从蛇形画廊展览上带走的两幅心理画是空白、静止的。这些广告牌“绘画”的美毋庸置疑;看到第一眼,我就希望能拥有一幅。在破坏公物的行为(偷旧广告牌违法?)和艺术的独立性(啊,单色画)混合中,暴露、消除并覆盖景观文化令人心智麻痹的噪音,如此相当于浓缩了朋克与现代主义,也让我这样一个长在八十年代(那时人们仍然相信艺术与批评能够带来变化)的女孩感到兴奋。但利登是在9/11事件之后才进入艺术院校学习。看她的作品,你会意识到,二十世纪艺术的乌托邦理想并不是关键所系。利登给出的空白和无声与其说是批判或解救之路,不如说是条件;与其说是规划,不如说是既定事实(缩减、回收、再利用)。在她的作品中,我感觉到一种心照不宣的承认:一切都已结束,当一名艺术家不过是又一种求生的方式,一种晚期资本主义现实里的生存策略。
另一方面,利登对静态的重新诠释也许能起到稍微不同的作用。她的“幻灯片”看上去极似模拟电视机无信号时的雪花屏。这让我意识到,这种静态正是数字时代缺少的东西之一。毫无疑问,信号不好或信号故障在今天也经常发生:只需想想手机里模糊不清的图像和声音,拖沓的网速和时断时续的Youtube视频。但拿着手机等待似乎永远无法完成的下载和沉浸于古老的电视图像故障(满屏跃动的光影,伴随着白噪音),两者的体验之间还是存在细微的差异。对我来说,后者连接着过去的时光,那时我完全相信艺术的救赎潜能,这种潜能不是超越性的,但是只想另一条道路、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利登临时制造的静态挡住了我的笑声,让我看到一线光亮,也许可以称之为希望吧;它让我从视觉和认知上慢下来,所以观看作品时,我感到的不是技术延迟带来的绝望,而是一种对内部认知时间的调整。我得等自己赶上图像的节奏,而不是等图像赶上我的节奏。利登的静里包含着一种弥散的能量,这种能量远远不是不可改变或无法移动的。
她的作品一直以细微但持续不断的努力,尝试战胜艺术在当今时代的速度和密度。所以,不管多么阴郁,她的展览还是成为我在2010年秋季所有艺术博览会上的解毒剂。
“克拉拉•利登个展”今年5月14日-10月9日在斯德哥尔摩现代美术馆展出。
海伦·莫尔斯沃斯(Helen Molesworth)是波士顿当代艺术馆首席策展人。
文/ 海伦·莫尔斯沃斯 | Helen Molesworth
译/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