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阿兰・巴迪欧;编辑:Antoine de Baecque,翻译:Susan Spitzer。莫尔登,马塞诸塞州:Polity出版社,2013年。共280页。《剧场狂想曲》,阿兰・巴迪欧;编辑/翻译:Bruno Bosteels。纽约:Verso出版社,2013年。共192页。《感知:来自艺术美学体制的若干场景》,雅克・朗西埃;翻译:Zakir Paul。纽约:Verso出版社,2013年。共288页。
阿兰・巴迪欧把哲学与艺术的关系比作雅克・拉康精神分析中主人与歇斯底里症患者之间的关系。歇斯底里症患者渴望一位主人向她解释她是谁,并将她未经处理过的真理变成能够传播的知识形式。但歇斯底里症患者-或艺术-无论得到什么样的解释,都永远不会感到满足。哲学给出的答案总是没说到点子上或不够充分,如此一来,他作为主人的地位最终将受到质疑。
为了维护自身权威性,哲学有三个选择。他可以采取果断行动,像柏拉图对待诗歌那样,下令将只能带来混乱的艺术驱逐出社群。或者他可以忽略这些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的要求,将其驯化,只享受它实际能带来的愉悦而不管其他。最后,他还可以宽容艺术,赞美艺术,承认后者包含着深刻的真理,而且这一真理正是源自其不可知。
难怪巴迪欧会狡猾地称赞他的同辈雅克・朗西埃,说他把“令人赞叹的歇斯底里”带进了哲学领域。朗西埃近年来对美学的关注并不是为了将哲学美学化,也不是为了赋予艺术以至高无上的价值,而是为了重新思考在艺术、政治和哲学中认知、感觉与思想之间的相互联系。写到这儿,补充一点知识历史背景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朗西埃的工作以及巴迪欧所开辟的另一条轨迹。
巴迪欧与朗西埃均已年届七十,各自的国际声誉也都正值顶点。两人同是法国结构主义那代人里剩下的最后一拨重要思想家。1968年五月风暴对他们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两人后来的发展道路在忠于这段历史的同时,又与路易・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保持了距离。后者在两人的知识成型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在五月风暴后慢慢跟共产党的“修正主义”联系到一起。朗西埃与自己之前的老师/合作者阿尔都塞公开决裂,意味着他否定了哲学家的主人立场,拒绝站在“知情”的一侧对仍然身处黑暗的另一边进行启蒙指导。他用来替代主人立场的是:一种不承认知识高于表象或科学高于感觉和认知的批判思想。哲学家必须愿意向艺术学习。
而巴迪欧从七十年代法国政治的全面退潮中看到的是一种重燃的迫切需要:我们迫切需要一种哲学去解释那些重要的稀有事件,这些事件能够永久改变我们对何为可能的认识和感知。在巴迪欧的语汇中,“事件”并不是指改变本身(无论其具有多大的世界历史意义),而是指那些为思想与行动提供新的突破口的事情;他给出的例子不仅包括68年五月风暴,还有格奥尔格·康托尔(Georg Cantor)有关无穷的数学概念,勋伯格的十二音列体系,以及任何两个坠入爱河的人。对他而言,哲学的功能是抵制按部就班的日常,思考并肯定新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笼罩在怀疑主义之下的那种漫无边际的批判思想就像一种歇斯底里症,必须加以抵制。就艺术而言,哲学必须避开上述所有三个选项:艺术不能变成唯一的真理,但在艺术里存在具体的事件,这些事件能够生产专属于艺术同时又具备哲学和政治意义的真理形式。巴迪欧在《电影》(过去几十年中他有关“第七种艺术”的论述文集)中告诉我们,关于艺术的哲学思考应该朝向一种肯定主义(affirmationism),“只有当它们暗示了能够改变世界的某个点,才能说艺术所催生的理念构成对世界的判断。”
最近翻译编辑出版的巴迪欧有关剧场(从1980年代至今)和电影(最早可回溯到上世纪50年代)的文集堪称他“非美学”里的重要章节。以巴迪欧的雄心来讲,当哲学尝试思考艺术的真理时,这一思考必须要能全面覆盖艺术整个领域。巴迪欧希望从某个具体的艺术形式内部找到真理独一的可能性,在某种实践的手段内部催生新的布局或新的理念。这就需要一种规范式的论述。在《剧场狂想曲》中,巴迪欧区分了“小写的戏剧”(theater)和“大写的戏剧”(Theater)。前者是指被称作戏剧的幻像,“一种天真无邪又兴旺发达的仪式”,而后者则是指“行动里的异端”,需要哲学对其进行回应。为了明确“大写的戏剧”的具体性,需要使其区别于其他容易与之混淆的艺术类型——没有可重复文本参考的表演,如哑剧或舞蹈,以及电影(电影院里原子化的观众不能跟剧场里的集体公众混为一谈)。
巴迪欧认为思考艺术是思考改变世界的一种方式,这一点也是朗西埃新书《感知:来自艺术美学体制的若干场景》的叙述核心,但朗西埃的目标显然与巴迪欧公理般的类型划分格格不入。《感知》是朗西埃迄今为止对现代主义标准概念最全面透彻的批判。根据格林伯格等人提出的现代主义叙事,艺术“必须将注意力从日常经验的内容上移开……转到其自身实践的手段上。”朗西埃想要说明,这种反动的现代主义就像一场迟到的防御战,它试图排除的是一种革命的艺术理念,该理念诞生于现代性内部,使艺术实践本身获得了清晰的轮廓,同时与格林伯格(就这一点而言,还包括巴迪欧)的主张相反,它“往往倾向于消除艺术的具体性,模糊艺术类型之间以及艺术与日常经验之间的界限。”因此,朗西埃的现代主义主流叙事批判中所涉及的介入不仅是在分析层面,也是在政治层面上进行的。他指出,不同艺术类型之间的融合在历史上跟艺术和生活(更具体地说,即普通人的日常经验)两者之间的融合密切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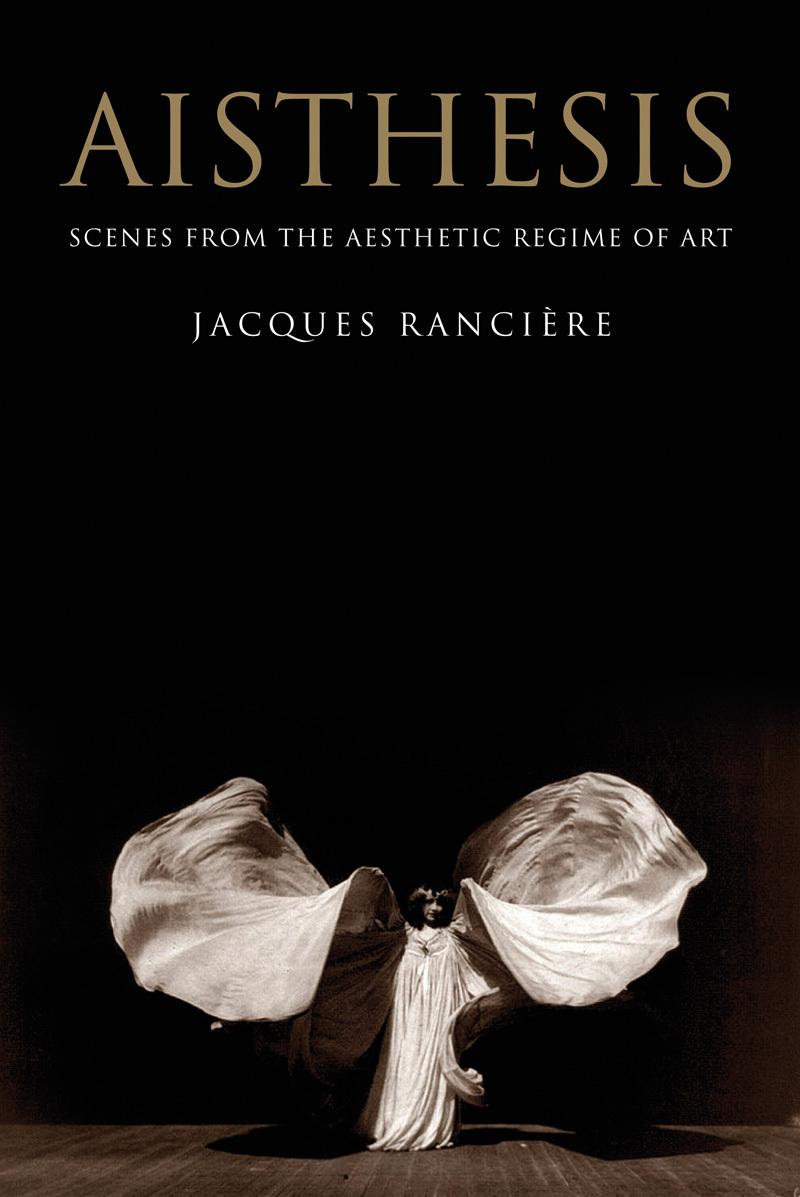
《感知》共分十四章,按时间顺序呈现了十四个“场景”。从1764年德累斯顿,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对贝尔维德尔英雄残躯(Belvedere Torso)的描述开始,到1941年美国,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和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的联合创作《现在让我们赞美名人吧》结束,这本书也许可被视为一段理念的物质史。每个“场景”均以一次具体的遭遇开篇,用一段引文揭示某件作品如何与有关艺术的新的思考方式产生联系。然后,朗西埃再梳理出该理念的逻辑,暴露其中的矛盾,使每段场景像戏剧那样逐渐展开,虽然每部戏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结局,但其核心矛盾会以一种新的而且常常令人意外的方式再度出现在下一个场景中。
现代主义学说不仅影响着一般意义上的艺术理论,规定着是什么因素促使某件具体作品成为典型,它更影响着艺术史的叙述。后者很少跨越学科边界,即便在我们这个所谓“后媒介”的环境下,艺术史研究仍然倾向于将小说、舞蹈、绘画或电影等领域分开来谈,而不是通过把这些实践揉到一起来思考艺术。正如朗西埃反复说明的那样,“媒介”并不总是单纯指某件作品或某类实践的具体物质性,而是至少意味着该物质性与某种艺术理念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将其与其他艺术类型以及某种生活理念紧紧联系在一起。
从《感知》呈现的“场景”中任举一例,易卜生的《建筑大师》在巴黎首演后,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写了一篇剧评,在文中提出一种新的戏剧理念,一种打破过去亚里士多德式戏剧行动模式的“静止戏剧”。但梅特林克关于“大写的戏剧”的理念,(借用巴迪欧的说法,以区别于“小写的戏剧”),从绘画的新方式里找到了自己的模范。同时,它也使梅特林克得出了一种关于舞台装置(mise-en-scène)的构想。几十年后,我们将从让・爱普斯坦(Jean Epstein)有关电影具体性的论述中找到该构想某种程度上的回应。在爱普斯坦看来,电影具体性正是在于把诡异的机械眼制造的新奇迹与其对戏剧的依赖分开。在这场具体性的流失中,我们跟巴迪欧的距离似乎远到不能再远。然而,巴迪欧在他有关电影乃是一种“不纯粹艺术”的理论中指出,电影融合了其他所有艺术类型,并模糊了与非艺术之间的界线,在这一点上他例外地跟朗西埃形成了同盟。巴迪欧为电影这“第七种艺术”保留了互相矛盾的结构与民主的许诺,而在朗西埃看来,这两点却是十八世纪末以来所有艺术的特征。
如今,我们经常看到“艺术界最爱”之类的说法出现在朗西埃名字前面,这是个明显的信号:一场批评界的反对运动近在眼前。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最近率先出击,指朗西埃为后批判转向的代表,不仅放弃而且全盘拒绝了批判的实践以及批判性艺术的范式。朗西埃在讨论艺术的政治时,提出艺术可以被看作一种对“感性分配”(le partage du sensible)的介入。福斯特认为这不过是朗“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且就像他在《十月》杂志和《伦敦书评》上发表的文章里反复提到的那样,也是 “艺术圈左派的精神鸦片”。
福斯特文章的攻击目标也许并不是朗西埃本人,而是他在艺术界各种小圈子里受到的热烈欢迎。只消看一眼《感知》封套上的评语就能知道艺术界人士的热情程度,这些评语大多是从《艺术论坛》杂志2007年的朗西埃特辑里摘录的:“‘朗西埃向我们展示了一条走出不安的道路。’——利亚姆·吉利克(Liam Gillick)”;“‘朗西埃重新点燃了对很多人来说已经熄灭的火焰。’——托马斯·赫史霍恩(Thomas Hirschhorn)。”讽刺的是,如果细数一下如今看起来还能跟艺术界产生联系的哲学流派,从后德勒兹式的生机论,到所谓的“感触转向” (affective turn),再到“思辨唯实论”(speculative realism)去政治的形而上唯物主义,或被命名为“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的对否定思想的全面拒绝,你就会开始觉得朗西埃的确是能够保持批评活力的最有影响力的当代思想家。
艺术可以被视为一个舞台,决定着可见、可说或可做之格局的日常感性和经验形式在这个舞台上能够被悬置、替换或颠覆——这一观点并非朗西埃独创,朗本人也从未宣称过这是自己的发明。但他所完成的工作是重新界定艺术实践的概念,通过承认艺术的政治潜能不可实现来保存该潜能。根据朗西埃的观点,“艺术”跟关于艺术的概念之间,感觉跟意义之间始终存在一种预设关系,即便(或尤其是)当前者宣称要抵制后者时。这一洞见把一大片陈词滥调的争论扫到了一边。艺术无法逃脱阐释(政治的也好,其他也罢),正如理论不可能为艺术提供答案一样。这是因为现代艺术理念本来就建立在矛盾的基础之上:艺术之所以能被构想为一个区别于理性、伦理和政治的自律领域,其前提是承认艺术的他律性,即艺术能够吸纳所有在历史上曾一度被美术拒之门外的日常经验。艺术不可能克服这一基本矛盾,而且也正是该矛盾为后来的发明和游戏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或者就像朗西埃在他2002年发表于《新左派评论》上的文章《美学革命及其后果》中所说,“美学的艺术承诺了一种它无法实现的政治成就,并由于这种暧昧性而不断繁荣。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希望把艺术从政治里单独抽取出来的人永远不得要领。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希望艺术兑现其政治承诺的人最后总是不免陷入忧伤。”朗西埃反复声称政治的艺术没有配方,一件艺术作品也永远不可能变成政治实践,如果读者想从他的书中寻找一条“走出不安的道路”,听到这里很可能会倍感沮丧。对这部分读者而言,巴迪欧的肯定原则也许可以成为一剂舒缓的解药。
巴迪欧可能会认为朗西埃为了维护现代性中艺术理念所包含的平等许诺而牺牲了把握具体艺术作品之激进新意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在朗西埃看来,巴迪欧把艺术的真理只留给那些能够重新定义其媒介潜能的特殊实践,如此做法很可能蜕变为划分界线的另一种方式,界线的一边是艺术,另一边则是普通人简单的享乐,后者曾被格林伯格贬斥为媚俗的生活。然而,朗西埃和巴迪欧所致力的哲学事业却有着重要的共通点。这种哲学不被怀疑或去神秘化的逻辑指引,但却忠于福柯对批评的定义,即:批评是一种“主动反抗的艺术”——这样的实践总会把哲学引回艺术身边,尽管前者永远不可能让后者满足。
尼克・鲍姆巴赫(Nico Baumbach)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电影学。
译/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