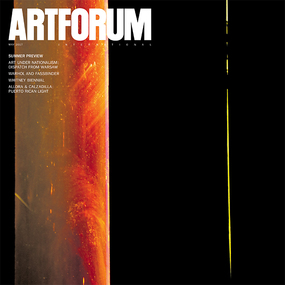来自CATPC(刚果种植园工人艺术联盟)的艺术家与IHA(人类活动学院)工作人员劳伦斯·奥托(Laurens Otto,左二)和尼古拉斯·周利(Nicolas Jolly,右)进行会晤,刚果卢桑加,2016年9月22日.摄影:Léonardo Pongo.
刚果种植园工人艺术联盟

在一个寒冷的一月午后,坐标纽约皇后区雕塑中心,一群学者构成了一个顶尖的阵容,面对为数不多的观众。他们这天的任务是来谈谈刚果种植园工人艺术联盟(CATPC, Cercle d’Art des Travailleurs de Plantation Congolaise)在展览中的作品。这些作品由荷兰艺术家伦佐·马滕斯(Renzo Martens)带来:十二座巧克力雕塑、一些纸本绘图,以及一部神秘的41分钟录像。然而台上没有一人能够真正说清楚这个项目:人类学家迈克尔·陶西格(Michael Taussig)通过讨论70年代哥伦比亚的前种植园农业来规避主题;摄影史学家艾瑞阿拉·阿祖雷(Ariella Azoulay)在帝国主义掠夺和现代艺术起源之间作了连接;艺术史学家大卫·乔斯利特(David Joselit)试图将马滕斯的项目阐释为“基础设施建设”(而非机构批判)然而也并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批判性评价;普林斯顿大学英语与非裔美国研究教授西蒙·齐康迪(Simon Gikandi)认为马滕斯成功地反思了艺术的商品模式。由于受到了过多的信息轰炸,提问环节期间现场几乎沉默了。我头脑发胀,对于马滕斯的项目,我并没有更清晰,反倒愈发困惑了。
无论如何,一种智性瘫痪似乎成为了马滕斯和CATPC、他和人类活动学院(IHA, Institute for Human Activities)——一个与CATPC密切关联的组织——之间合作的主流反馈,这些合作耗费了艺术家自2012年以来的所有精力。他的早期作品——富有争议的散文录像《第一季》(2003)和《第三季:享受贫穷》(2008)——都落入了纪录片反叛这一已被认可的类型。在前者中,艺术家去到格罗兹尼并问当地的车臣妇女她们是否觉得他有魅力;在后者中,他鼓励刚果摄影师利用自己的贫困作为经济资源来贩卖苦难的图像。这次与CATPC的项目中,马滕斯超越了再现,进行直接的介入。IHA目前拥有位于卢桑加市郊的五十亩地,工人们把那里当作农业和艺术创作的基地。这似乎将IHA变成了地主,还变成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历史上排着长队的白人剥削者中的最近一位——考虑到机构是由马滕斯和他的艺术家同行雅各布·科斯特(Jacob Koster)和德尔芬·海斯特斯(Delphine Hesters)共同创办的,他们都是欧洲白人。值得欣慰的是,马滕斯自己并不否认这个事实。
在座谈讨论期间,马滕斯用了一个术语:反士绅化(reverse gentrificaton),以此来概括一个他反复强调的观点:当代艺术周围流通的金钱总是逗留在全球艺术市场的中心,而不是流回那些偶尔构成了其艺术题材的地方。IHA的目标是挑战这一点,将盈利返还到外围经济中。如此一来,受益者是卢桑加的农民,他们在之前仅仅能维持生计,而今有了第二重身份:职业艺术家。他们的黏土雕塑经过3-D扫描,然后被送到阿姆斯特丹进行3-D打印,再用巧克力浇铸;之后,这些作品被展示和销售——以超过5000美元一版的价格,小的头部肖像售价42美元。这些收入有不同的用途,主要用以在这片前种植园中开发对环境负责的农林业技术。然而重要的是,马滕斯希望CATPC不仅仅从销售这些艺术品来赢利(太基本了),还从对作品的批评中——于是就有了在雕塑中心这全明星学者阵容,系列座谈中的第四场题为“批评事宜”。知名评论家和学术界的注意力生产出了文化声望,马滕斯认为工人同样也从这些讨论中获益了,因为他们的劳工如今生产出剩余价值。
马滕斯正在与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的蓝筹建筑公司OMA合作在IHA的土地上设计一座博物馆和一座会议中心,他们收到了无数文化机构和学术伙伴的资助。马滕斯声称这是“对白盒子的复仇”,并有说服力地表示自己想要“重新连接”画廊与种植园,因为这两种机制一直以来都以互相无视的状况共生着:利物浦的雷福夫人艺术画廊建立在售卖用以制造肥皂的棕榈油的利润上;伦敦的泰特画廊的创立与甘糖贸易分不开;科隆的路德维格博物馆用艺术来清洗巧克力加工的收入,并且也从棕榈油生意中获得资金;这个名单还有很长。当代艺术界因其资助者对非洲有着浓厚的企业家兴趣,因此持续地剥削着这块大陆——比如说,在2000年至2012年期间,泰特现代所有的特拜恩厅委任项目都是由联合利华资助的,这家公司一直在刚果拥有种植园。那些创作参与性摄影或录像的艺术家实践着一种愈加直接的利用形式。
马滕斯第一个承认他这个项目里面充满悖论的“既包容又暴力”的特征,他将其描述为是一种机构批判实践:曝光艺术界的矛盾和虚构,揭露那些受益于现代蓄奴业和其他不义手段的艺术机构对展示良心艺术的喜爱。同时,他明确地希望在当地和在CATPC的艺术家-工人中间造成正面的影响。但是鱼和熊掌是否可以兼得?伦理上有问题的新殖民主义企业资本主义的过度识别 ,是否可能与伦理上说得过去的社会参与形式齐头并进?还是这两股相反的力量互相抵消了呢?
这样一种“两面派”的情况直指CATPC所引发的困惑的核心。这个项目势必会使一些自由派的艺术观众感到不适,如果我们不管马滕斯那煽动性的言辞,这整个项目有点像是一种社会经济实验,或者新型NGO(但是是一个难以被分析的NGO,因其财务不透明)。项目中其余部分具有社会实践类艺术常有的问题。在那些意图超越再现并对现实状况产生影响力的艺术中,我们如何衡量效力?

在过去,类似项目的成就多少是好坏混杂的。IHA将自己与其他连结了国际艺术界和偏远的非西方地点的长期艺术计划进行比较,诸如1998年由泰国艺术家里里克力·提拉瓦尼加(Rirkrit Tiravanija)与卡明·勒差布拉瑟(Kamin Lertchaiprasert)在清迈城外建立的实验农田项目“土地”,以及1997年丹麦团体Superflex在坦桑尼亚建立并经营的沼气系统。沼气项目最终成为了可持续的当地能源,但是当我2006年拜访“土地”时,该项目却有所降退。从农业层面来看,项目是失败的,而奇形怪状的建筑亭台(由菲利普·帕雷诺[Philippe Parreno]和其他关系美学谱系的成员创作,这些艺术家还将那个场地拍进他们的录像作品)也是荒凉而杂乱。然而,一个更加引人深思的类比可能在美国,在西斯特·盖茨(Theaster Gates)的实践中:他通过销售拼装、绘画以及陶瓷作品获得利润,用以获取并整修芝加哥南边的(South Side)房屋(这些房屋反过来为他的拼装作品提供更多材料)。马滕斯和盖茨都与士绅化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但是盖茨的项目中各个方面都有可以被清楚辨识的美学,使得项目虽然分散在不同的场合中却能保持视觉和概念上的一致。
相比之下,马滕斯的双刃剑项目缺乏美学辨识度。白立方的展厅与种植园(其中共有6650棵可可树、801棵油棕榈树以及944棵果树)形成了刺眼的对比。这样的断裂是有力量的,但是巧克力雕塑又是另一回事:它们的生产演绎了全球经济网络,但是它们的样子主要还是人物形象,而且并非总是关于跨越几代人贫困、剥削、忍耐以及反抗的故事,虽然这些主题是它们想要传达的(一件来自塞德里克·塔马萨拉[Cedrick Tamasala]的作品题为《我的祖母是如何生存下来的》,2015)。这些雕塑的图像学究竟如何才能与当地甚至刚果过去与现在整体的美学生产发生关联?如何与马滕斯对艺术界的世界级批判发生关联?明了的是,这些雕塑作为单件作品的意义位于它们在经济与文化资本网络中所起的角色之后——这一点在它们在雕塑中心的展示中更加激化了。它们被孤立地置于一个洞穴式的展厅,其中有三件作品令人费解地以三联像的形式被呈现。
刚果依旧被殖民主义后遗症所笼罩。这段历史对马滕斯有着深重的影响,包括在比利时统治下那令人难以想象的暴行。“我需要做这件事,并不是说哪怕我是白人我都要做,而是正是因为我是白人我才要做,因为我被帝国世界的利益所喂养,”他在最近的一个访谈中说道。一个白人欧洲人需要技巧才能在这段历史中进行有意义的巡航。马滕斯希望通过人物形象的雕塑来对艺术经济进行系统性的批评,但是该项目无法传达其所希冀包裹的讯息,因为艺术家从根本上对物件没有兴趣。顶多,作品中机构批判、社会实践、替代经济以及过度自我辨识的融合成为一个让人不安及富有挑战性的命题。如果缺乏美学中介,马滕斯项目中激活的两种艺术模型——IHA的机构批判和CATPC的物件生产——在进入彼此的语境中时变得不清不楚,让人疑惑。如果这其中的张力能够在美学层面有所体现的话,如果形式能够被动用起来以传达再现与介入之间之辩证关系的话,马滕斯的任务则会更加具有切实的颠覆力,甚至鼓舞人心,而不是不知疲倦地对我们的良心喋喋不休。
由OMA设计的“白立方”,作为卢桑加国际艺术与经济不平等研究中心的一部分,已在4月21日对外开放.
克莱尔·毕晓普是纽约城市大学艺术史PhD的教授.
译/ 张涵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