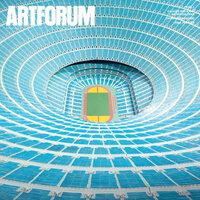托马斯·赫赛豪恩(Thomas Hirschhorn)的“假作假时假亦假”(Fake it, Fake it-till you Fake it.,2023)以一个轻巧的干预开场——很可能是这场典型的赫赛豪恩式的混乱展示中(艺术家对“装置”一词颇为厌恶)唯一轻巧的部分:一段延伸的硬纸板将格莱斯顿画廊(纽约21街空间)的门厅和主展厅隔开,使入口通道变窄,从而限制了从外部观看作品的可能,确保人们只能从作品那咆哮的“大口”内部看到它的全貌。整件作品形同一间错乱的军事控制室,其布置仿佛出自嗑了阿德拉(Adderall)和牛磺酸的游戏玩家的臆想,其质感则像是出自手巧的学龄前儿童之手。在这里,硬纸板制的桌子上摆放着一排排硬纸板制的键盘和显示器,由胶带固定,还有满架子的硬纸板智能手机和硬纸板平板电脑,用打结的胶带和皱巴巴的锡箔线充当充电线,按键则是用黑色记号笔匆忙画上去的。

在这些数量庞大的假设备的屏幕上,显示的是未标明具体出处的各种暴行的电脑打印低质图像。其中一些明显是第一人称射击游戏截图,画面角落还保留着提示剩余生命值、弹药或最高分数的小图标;而另一些则可能是记录真实灾难——尽管几乎无法辨识,或至少是无法确定的——的照片或录像静帧。这两类画面大部分让人难以区分,而这并不奇怪:现在的游戏做得越来越精细,军事袭击则越来越拟真,至少对袭击者来说是这样。今天,无人机在也门发动的袭击,最有可能是从内华达州的一个“黑匣子”里通过摇杆进行的。而在这里,屏幕上的暴力似乎逃脱了它的边界,其不稳定性使之难以被限定在元宇宙的假想空间中,而是折返回来摧毁了整个房间。为了阐明观点,潦草喷涂在一面展墙上的伪宣言警示着我们向虚拟世界过度退让的危险性。“我们在讨论的是‘人工智能’——但为什么只是‘智能’,而不是‘人工意志力’?‘人工信仰’?‘人工信念’?‘人工希望’?‘人工抵抗’?‘人工直觉’?”, “永远不要为了摆脱机器人的控制而放弃‘智能’以外的人类能力。保持警觉,否则你将成为下一个猎物。”

和赫赛豪恩的许多作品一样,《假作假时…》呈现了过剩与贫穷(或者借用艺术家喜欢的说法,就是“不稳定/precarity”)之间充满矛盾的较量。其创作手法在任何意义上都显出寒酸——廉价、易得、不符合档案保存的标准——并且组装粗糙,毫不考虑使用寿命或稳定性。艺术家的座右铭是:“要能量!不要质感!”然而,整个环境却显露出一种狂躁的享乐主义特征,将观众带入一个失常的个体世界,赫赛豪恩曾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垃圾桶”:由锡箔纸和印刷品组装的压扁的红牛饮料易拉罐散落一地;键盘掩埋在成堆的泡沫塑料烟头和可卡因之下。在入口的一角,一堆硬纸板废料从天花板倾泻下来,淹没了其中一个工作站;一些显示屏被击碎,尖锐的碎片洒落在周围。与此同时,用胶带固定的各种emoji表情符号从天花板上垂落,而穿插在这些在智能手机时代被用烂了的通用语之间的,是用计算机生成的、几乎与真人一般大小、身穿各式军装的士兵半身像。这些纸板哨兵堵在不同的过道处,迫使观众自行决定要以何种态度来面对它们:一些观众索性将其推开以便通行,另一些则恭敬地绕过这些脆弱的障碍物。展厅后侧放置了一台巨大的工业风扇,在其吹拂下,纸板随风扭动,当人们在展厅中移动,也会感觉到风扇的风力在逐渐增大:展厅入口处,士兵和笑脸表情像婴儿床上的风铃一般轻轻摆动;而到了展厅后侧,它们被疾风猛烈吹动,固定的胶带粘在一起纠缠不清,变成一个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卡通表情超合体。

“如何在战争、破坏、暴力、愤怒、仇恨和怨怼的时代里创作艺术?”赫赛豪恩在艺术家陈述中问道,“在黑暗和绝望的时刻,我们应当创作什么样的艺术?”他给出的答案是,将残暴放大至歇斯底里的程度。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称之为“模仿式加剧”(mimetic exacerbation),在他看来,赫赛豪恩的关键操作便是“挑出坏事并使其变得更糟。”这种策略传承自雨果·鲍尔(Hugo Ball)等苏黎世达达主义者,一百年前,鲍尔将坐在安全的瑞士咖啡馆里观看世界烧成灰烬的荒诞经历转化为一场尖刻的滑稽表演;到2000年代,即9/11事件爆发和美国进攻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后(另一个整个世界似乎突然集体丧失理智的时期),该策略曾一度成为或重新成为了一种主流的艺术实践模式。其有效性在于,通过夸大社会中最怪诞和堕落的形式,对其施加压力,使其变得更加诡异,从而让人能重新看见它们,而且看到它们真实所是的恐怖样貌。

难怪我对《假作假时…》的首要印象与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有关,它让我想起赫赛豪恩为回应伊拉克战争而创作的一系列作品,特别是2006年同样在格莱斯顿画廊举办的展览“肤浅的交战”(Superficial Engagement),后者亦由占据整个展览空间的废弃材料组成,其核心也是异质图像的密集并置:当时使用的图像包括因美军炸弹而致残和死亡的无名死伤者惨不忍睹的照片,以及二十世纪初瑞士神秘主义者艾玛·昆兹(Emma Kunz)空灵飘渺的抽象图画。关于那场展览,大卫·乔斯利特(David Joselit)在发表于《艺术论坛》的评论中写道:“赫赛豪恩将血肉模糊的肢体与抽象的疗愈对立呈现…拆穿了美国世界的虚伪性,在这个世界中,毁灭性的轰炸被宣传成’精确打击’,而制定作战计划的则是哈里伯顿公司。”这种循环性似乎正是重点所在。这次在画廊的一面展墙上,贴着一张颗粒感十足的黑白巨幅照片,描绘了另一条被炸毁的街道,但这条街道更为古老;我猜想它可能是二战时期的街道,但悬在半空中的emoji表情却将整个场景挡住,让人难以辨识出任何比瓦砾更具体的东西,如同一则关于我们逐渐退化的历史意识的残酷隐喻。赫赛豪恩在艺术家陈述中提到,他希望这件作品可以成为一个“反思的平台”,而它所反思的——就像游乐场里的哈哈镜一样——则是一个从未能吸取任何教训的患遗忘症的文化。

然而二十年过去了,我怀疑这种方法换来的是越来越少的回报。面对这样一个社会——电视真人秀明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受到四起刑事起诉的前提下,正再次竞选美国总统,并很有可能获胜——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其荒谬性进行有意义的夸大?更重要的是,与社交媒体真实推给我的内容相比,我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它更丑陋不堪、利益至上的粪池,它吸纳每一种恐惧、仇恨思想和低级欲望,再以可消费、易消化的发帖形式将其喷吐出来:可直接发货的1950年代复古山寨货、适应原补充剂和神奇塑身衣的广告,紧挨着已死或垂死的儿童、新纳粹meme和化妆教程。(它们有时会结合成令人作呕的杂交体:比如,色列国防军预备役军人纳塔莉娅·法德耶夫(Natalia Fadeev)贴出来的性感自拍,或“男权文化圈”[manosphere]骗子、被指控人口贩卖的安德鲁·泰特[Andrew Tate]在TikTok上兜售加密货币及厌女言论。)相比之下,赫赛豪恩的低保真警告似乎已经过时。但他提出的问题却并未失效:“如何在战争、破坏、暴力、愤怒、仇恨和怨怼的时代里创作艺术?”不仅是赫赛豪恩,最近的很多艺术实践似乎都在我们的极端处境中呈现搁浅状态。或许,我们可以从赫赛豪恩的项目中吸取的一个教训是:没有人能够在逐底竞争中真正获胜。
展览“托马斯·赫赛豪恩:假作假时假亦假”在纽约格莱斯顿画廊持续至3月2日。
蕾切尔·韦茨勒(Rachel Wetzler)是《艺术论坛》的资深编辑。

文/ 蕾切尔·韦兹勒
译/ 钟若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