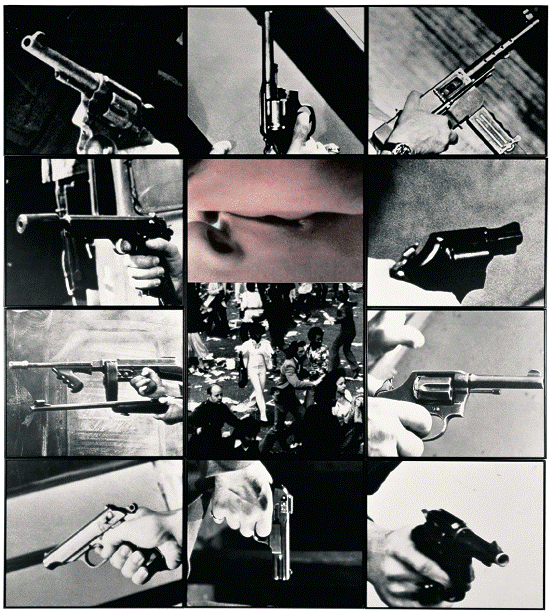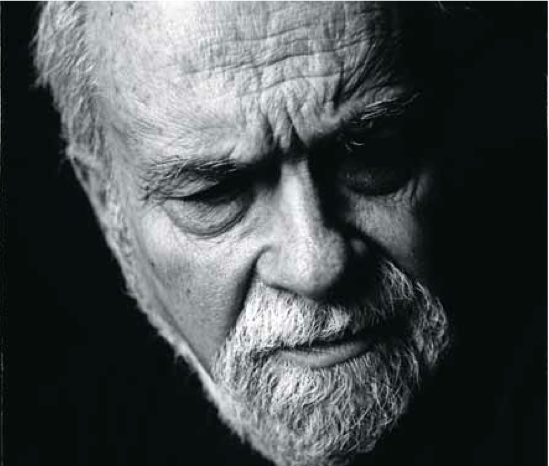卡斯腾•郝勒的双重俱乐部
前段时间,我去了一家“当刚果遇到西方”的酒吧/餐厅/夜店。几个星期后,我又去了一家“当西方遇到刚果”的酒吧/餐厅/夜店。两家店都位于东伦敦的一条小街(7 Torrens Street)上,所以你可以说它们是同一个地方。但去年十一月卡斯腾•郝勒(Carsten Höller)在Prada基金会赞助下创办的双重俱乐部(Double Club,今年年底就会关闭)如此强调矛盾和双重复制,以致于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同一性变得越来越淡薄。在酒吧入口,你就得决定到底进入哪一“片区”——放着颜色明亮的塑料椅和木质吧台的“非洲”区(Bellou Luvuadio Bengo设计)还是装点了大量霓虹灯和金属台的“欧洲”区(Reed Kram和Clemens Weisshaar设计)。实际上,整个空间都像切蛋糕一样被分成了若干块:从地板上划分的楔形区域可以看得很明白。这一几何图形也出现在旁边餐厅挂的瑞典传奇现代派艺术家奥列•拜特林(Olle Bærtling)的油画上。拜特林在《开放形式宣言序》(Prologue to a Manifesto of Open Form , 1971)中曾说,他希望自己的画成为“宇宙的一部分,一轮红日,一个传播诗意讯息的力量中心”,以“释放无限”。谁知道呢——也许这就是他的作品最终完成的释放:为这家自由“浪荡子”聚集的时尚夜店提供蓝图设计。在人多的晚上,你可能撞见米克•贾格尔(Mi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