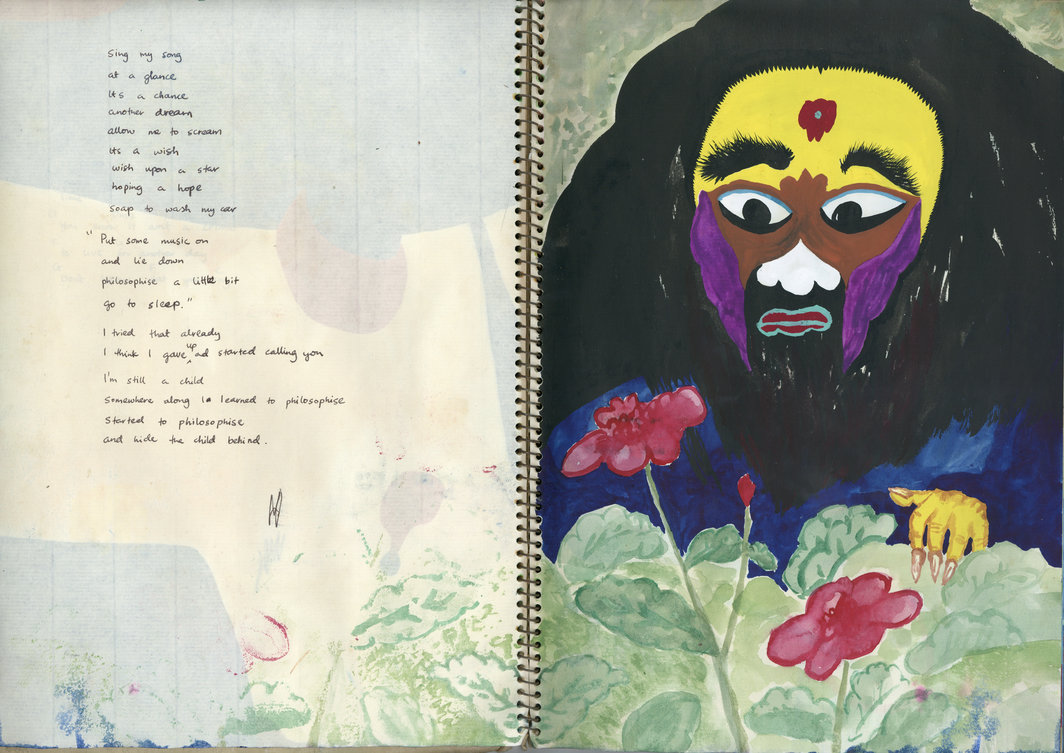每当变幻时
3月20号抵达香港,在还没有开始任何的艺术类行程时,我决定与之前一起生活了四年的室友吃第一餐晚饭。前室友是一名香港独立平面设计师,同时一直致力于艺术和本地社区结合的项目。她告诉我:“你搬走后的四年,这里发生了很多变化。很多朋友离开了香港。”听完后我的心情复杂,尽管这里不再是我的居住地,而且和很多人一样,疫情爆发以来就一直没有机会再访,但香港好像始终给我一种“故园风雨后”的熟悉与陌生。室友说到他们在申请艺发局项目资助的时候,需要上一门关于国安法的课程,很多艺术家的项目也可能不再被批准。我在庆幸我的粤语没有退步的同时,也发现她的普通话变差了。
饭后我们一起去了M+的派对,但很快在现场人潮的冲击下分散告别。费了一番力气,我终于找到约定在这里碰面的几位香港艺术家和策展人朋友。几轮紧紧的拥抱过后,大家的眼眶都有点湿润。音乐声很大,但也盖不过周围不断发生的久别重逢的欢呼和问候。聊不完的话题、不知从何讲起的经历,当然也不缺为明天即将开幕的博览会热身的职业客套。尽管现场音乐到位,大家似乎无心跳舞,重启的积极氛围背后多少也能感到些许忐忑和谨慎。
第二天的会展中心,香港再次用它的高效证明了这里依然是资本和机遇在亚洲流通的最佳中转站。我跟艺术家杨沛铿约在他这次参加巴塞尔博览会“艺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