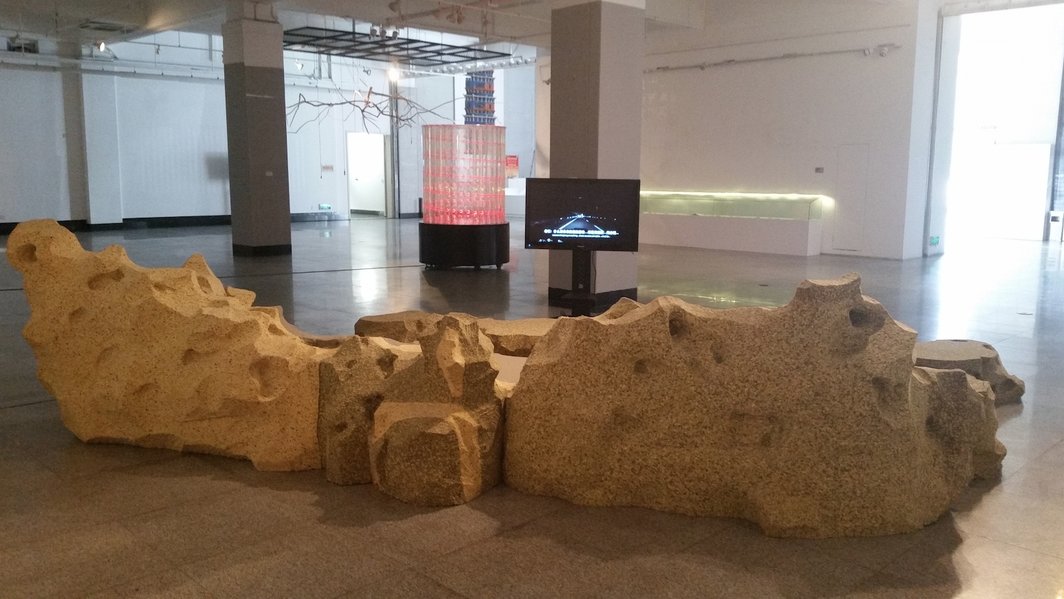刘夏:HOLY PAINTING
说话、走路和想事时手习惯性地插在套头衫的侧兜,这是刘夏的标志性姿势,就像他的作品《休息中的耶稣》(2015)中叉腰低头的耶稣,让人联想起令马丁· 基彭贝格(Martin Kippenberg)遭到巨大争议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青蛙《Fred the Frog Rings the Bell》。相比基彭贝格的渎神嫌疑,刘夏在充分表现出尊崇神性的同时,也流露了某种无可奈何的情绪,他试图改变耶稣与十字架之间经典主义的图形构成,令其产生两个主形相互叠压的关系,使十字变成一个不规则形。
对绘画呈现的叙事,画面本身的样貌,或者对某一场景的想象,都有可能是刘夏下笔的切入口,就像是一部小说的故事性往往由第一个矛盾引出,并由接二连三的转折勾连出一整套故事线索,刘夏的绘画也是在这种互相咬合与平衡中展开。《军医》(2015)中,涤荡心灵的神性在此被置换成为拯救肉体的医生形象,这两种对立的角色在“偷换”中被放置在一个有趣的着力点上,而黑色皮肤恰恰在古典主义绘画中是罕有的主角,在此人物被融入委拉斯开兹式的经典暗部背景之中,反而违背了绘画的色彩原则,幸好有一身白色大褂,才让人物主体从黑背景中跳脱出来。橄榄绿的裤子被红色的边缘线勾勒出的形状,让人生起某种隐约的不安与荒诞感——他不但是医生,还是一个穿橄榄绿的军医,这时我们突然注意到,“黑军医”手里夹着的白色香烟成为了画面的刺点。
出身基督教家庭的虔诚与个体诉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