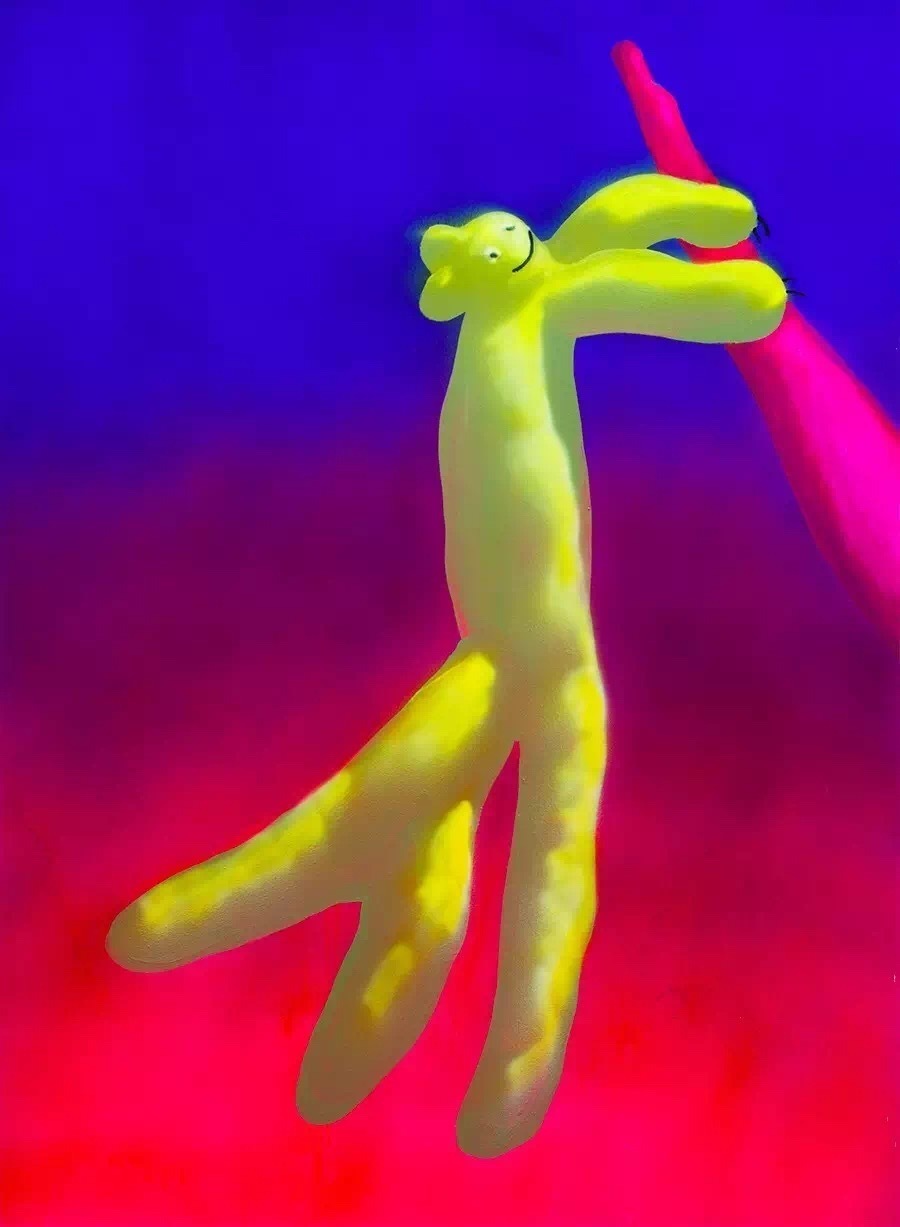回不去的北京
11月8日一下飞机,我就拖着行李箱直接去了上海明当代美术馆,赶毛继鸿艺术基金会和蓬皮杜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重置时间”论坛最后一场对谈—“重塑机构现实”。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跨学科文化发展部主任凯瑟琳·魏尔(Kathryn Weir)作为对谈主持,邀请4位嘉宾质疑“机构”这一概念,在回溯它所发挥的传统功能的同时,反思机构在技术加速革新的当下能够起到的作用。奥地利哲学家阿尔曼·阿瓦尼斯安(Armen Avanessian)观察到,我们正经历从现代到当代,哲学到理论的历史转向。艺术在本体论上的不稳定性增加了我们对理论的需求,每隔五年甚至是两年便催生出一套新的理论工具。邱志杰以自己的多重身份分享了他挑战不同机构/机制的尝试。担任明当代馆长的他,试图在表演艺术与视觉艺术的中间地带建构一座难以被娱乐化消费的美术馆;“被迫”做策展人的邱志杰,调侃自己2012年用城市馆取代威双国家馆的方法没有在接下来的两届上双延续,算是构建新展览模式的失败;作为艺术家,他以雅集的形式把工作室变成平行于非营利机构的展示空间。在Q&A环节,毛继鸿艺术基金会学术总监贺婧的压轴提问将讨论延展到艺术家在体制内外所面对的中国特有的机构现实。邱志杰的回应如同明当代的定位一般in-between:我们可以利用体制内松动的部分进行向外的变革。
由付了了策划的“流动者会议”(Precaria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