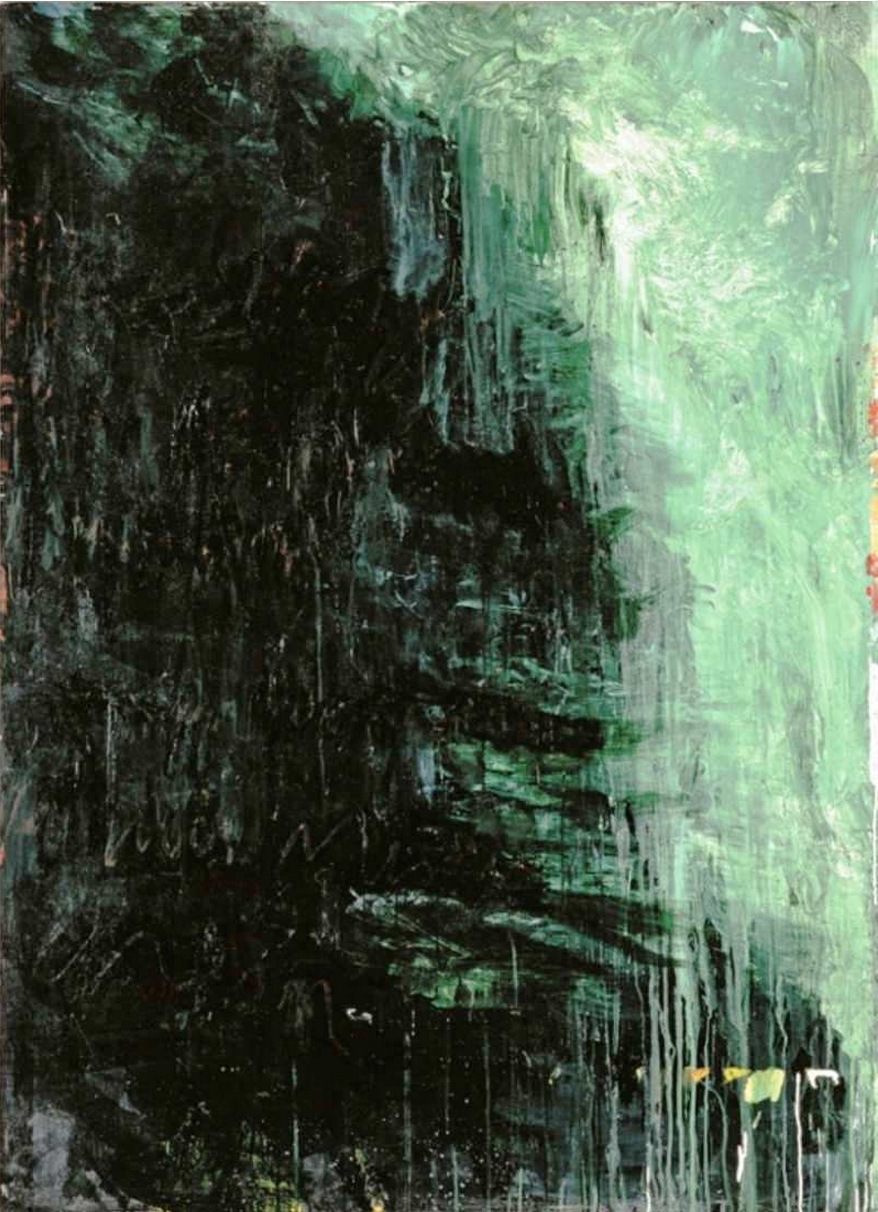外冷内寒
到了电影节的第八天,我知道自己也中招了。当我在观看正午的洪尚秀《大自然对你说了什么》(What Does That Nature Say to You,2025)媒体场放映时,我加入了此起彼伏的咳嗽大合唱:还是没躲过那可怕的“柏林影展流感”。在每日新闻的残酷轰炸下,再加上持续不断的零下寒潮,每当我们走出影院幽暗的洞穴,进入外面那病态惨淡的白昼,就仿佛全球范围内步步紧逼的法西斯主义正侵蚀着我们的身体。而这场病的唯一慰藉,便是银幕上散发出的那一丝人造的暖意。
在这部讲述一位年轻诗人首次拜访女友父母的新片中,洪尚秀巧妙地在冷与热之间找到了平衡。虽然这位导演惊人的高产(有时一年能拍三部长片)使得他的作品总带有某种公式化的特征(陌生人尴尬相遇,彼此过度礼貌,直到酒后情绪爆发),但《大自然对你说了什么》仍精准地讽刺了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新儒家僵化礼教及其背后的脆弱人性的讽刺。洪尚秀的电影要么让人沉迷,要么让人厌倦,我坚定地属于前者。
杜拉·裘德(Radu Jude)对国家内部问题的审视要严厉的多,凭借对祖国罗马尼亚富有幽默、思想性和诗意的挖掘,他成为了各大电影节的宠儿(《倒霉性爱,发狂黄片》[Bad Luck Banging or Loony Porn]在2021年柏林电影节摘得金熊奖)。今年荣获最佳剧本奖的《二〇二五年的欧陆》(Kontinental ’25)再次以微缩史诗的形式呈现,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