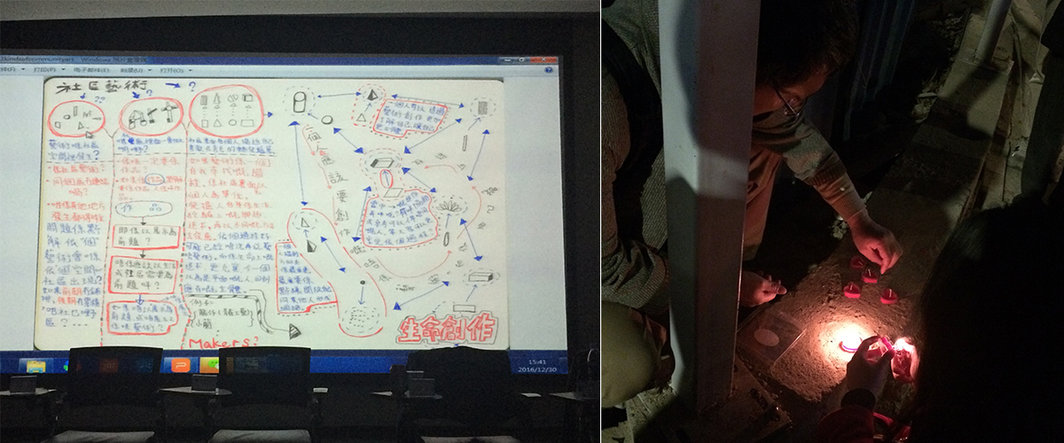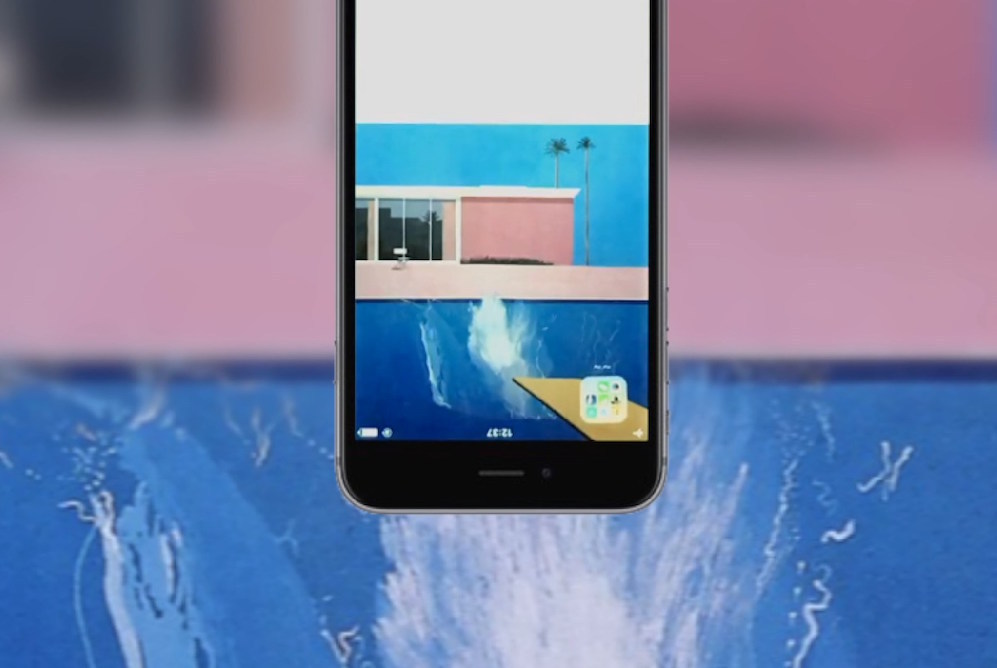郑源
此刻,我在俄罗斯航空公司的飞机上一边敲打键盘,一边回想几天前进入泰康空间二楼“日光亭”看到的第一个视频:香港电视剧集里,一家人从新闻中听到自己亲人所搭乘的客机坠毁;随后,一个无情感的声音开始讲述1983年9月1日一架大韩航空的民航客机严重偏航,被苏联空军误认为在执行间谍任务而遭击毁;为避免同类事故再次发生,美国政府决定将GPS开放民用。而当下中国发达的数码平台服务和电子商务—地图定位、外卖服务、共享单车等—都是基于GPS民用化。旁边的电视里播放的是2003年并入东方航空公司的西北航空的广告(该航空公司在艺术家郑源的家乡兰州曾设有分公司)。这是有些吊诡的溯源式的《一个(乏味的)晚上:新闻,广告和历史频道》(本文提到所有作品均创作于2017)。
《一段(简短的)历史:曾经占据过这片天空》细数西北航空解散后作为货物的飞机被卖到哪里,描画出关乎地缘政治的地图。而《一次(失败的)飞行:酒泉航空站》中,无人机镜头下五十年代中苏共建的机场的废墟,则暗示了曾经支撑飞机移动的物质和体制变迁。如果说飞机舱内的空间是个面目模糊、时空不明、移动的非地点(non-place), 乘客们将自己交付给陌生的飞行员,一切都悬在半空(up in 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