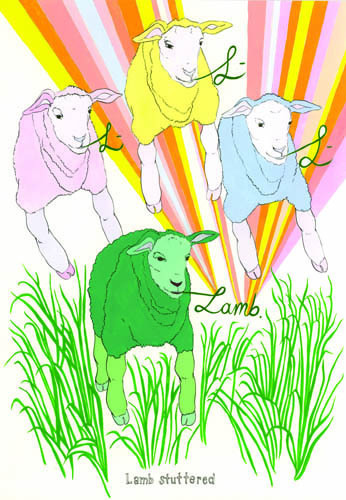去而复返
香港巴塞尔开幕前,Eaton House放映了英国艺术家Robert Crosse的短片,其中包括新片的粗剪版本,是他在“彼岸观自在 V”项目驻留一个月的创作成果,这个项目是香港的videotage和英国的videoclub间的第五次合作。Crosse的影片经常涉及老年和跨代酷儿关系。香港驻地期间,艺术家花了很多时间了解当地老年酷儿社群。在放映后与江绍祺(Travis S.K.Kong)的对谈中,Crosse谈到自己能够意识到自己作为局外人的身份,而且如何在视觉上表现香港的酷儿社群对他来说仍是个未解决的问题,其中很多人还没有完全出柜。
巴塞尔开幕前一天,我去了几个人满为患的画廊展览开幕,马凌画廊的新展是新加坡艺术家何子彦令人赞叹的作品《东南亚批判性辞典》(2012至今)的最新章节。我见到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当代艺术部新任总策展人陈畅(Abby Chen),她正在和藏家曾文泉(Rudy Tseng)谈论建立博物馆的当代艺术收藏。我还碰到了艺术界的人类学家Sarah Thornton,她说道,“香港是最原初的全球城市……是民族志学者的天堂。”
在新闻发布会上,Marc Spiegel说这届展会真正是“最全球性”的一次,因为有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242家画廊参展。不过出人意料的是,他说他也同时希望指出不那么令人激动的一面——现在全球各地画廊所面临的困境。那天,我还瞥见了瑞典演员Aleksan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