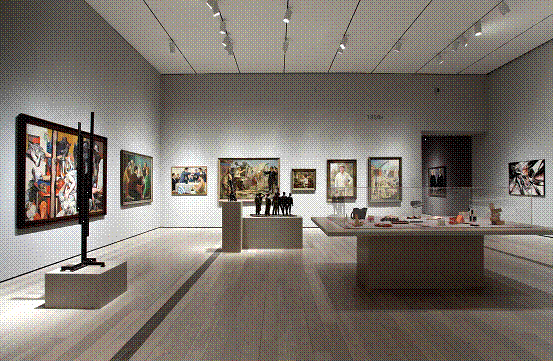(非)团体的团体:丹尼尔·布伦和BMPT
1966年到1967年,丹尼尔·布伦(Daniel Buren)和他的同伴奥利维尔·莫塞(Olivier Mosset), 米歇尔·帕尔芒捷(Michel Parmentier), 尼埃尔·托农尼(Niele Toroni)以各自姓氏的结合体为名,对新前卫艺术进行了一系列近乎景观化的激烈批判。要是让居伊·德波(Guy Debord)对布伦等人这一时期的活动做出评论的话,他必然会先于众人看出在四人创作实践中存在着自己十年前抨击Yves Klein作品时发现的事实:在资本主义消费的整体环境下,景观和新前卫艺术激进派不再互相排斥,而是越来越多地互为补充,彼此加强。至于布伦,他对字母主义和情境主义国际的历史及策略知之甚详,后来搞到情境主义文本和资料最全面的系列收藏之一,早年对景观(spectacle)和异轨(detourment)的兴趣可谓没有白费,甚至连他家起居室的入口都装点着德波和阿斯格·约恩(Asger Jorn)号召立即消灭异化劳动的海报画。
相比之下,罗兰·巴特和米歇尔·福柯(艺术家另一个隐藏的哲学家神)都没有注意过布伦或BMPT。进入当时哲学家视线的是让·德戈特(Jean Degottex),热拉尔·弗罗芒热(Gérard Fromanger)以及后来的塞·托姆布雷(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