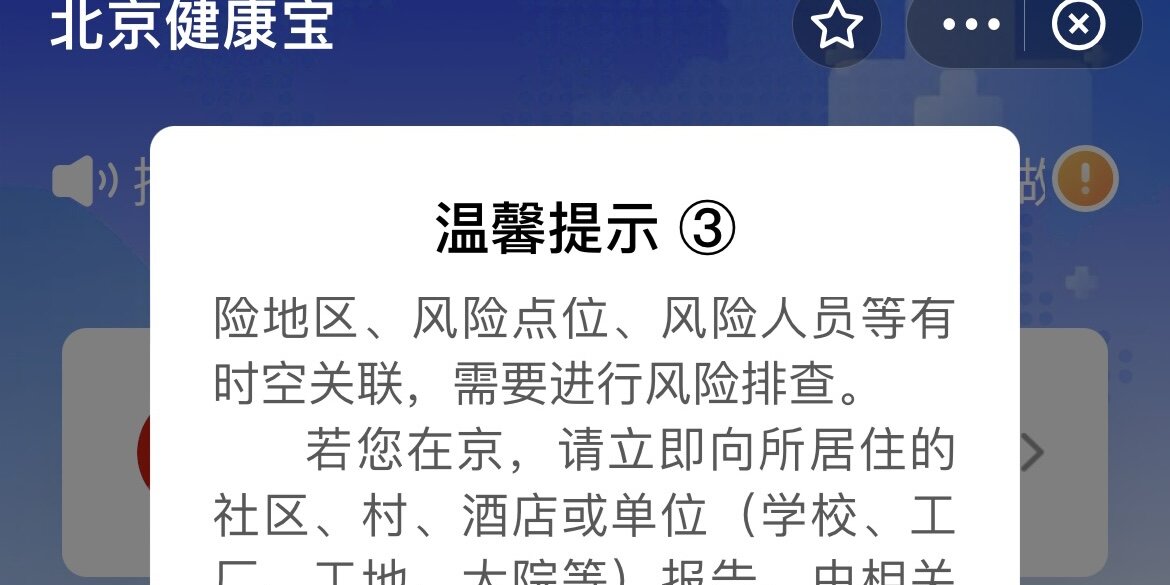
愿你活在有趣的时代
今年的上海艺术周让我想起三年前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愿你活在有趣的时代”。这不仅是因为在油罐艺术中心看了埃德·阿特金斯(Ed Atkins)的展览“无用之物”后所激发的记忆蒙太奇,而且更像是在见证一连串带着后见之明看或许并不太过出人意料的现实事件后,顿悟般看清了这句暧昧不明如同谶语般的祈使句被解签后的样子。
11月7日,立冬的上海温暖如春。和朋友相约去延安路上的双叶居吃热气羊肉,为即将到来的艺术周积蓄能量。当晚的“前菜”是没顶画廊汪建伟的展览“行于泥浆”(由陆兴华策划)和Chi K11美术馆卡洛琳·沃克(Caroline Walker)描绘女性日常的绘画展“被看见的女性”;有趣的是,近日出版的《看不见的女性》一书的作者也叫卡罗琳(Caroline Criado Perez)。当晚朋友圈刷屏的,则是程然组织的派对“老友鬼鬼”上单人单管的试管酒,一种将恐惧和倦怠转化为沉醉和愉悦的荒诞疗法。
艺博会开始前两天,M50、外滩、安福路及西岸的画廊与美术馆新展纷纷开幕,其中一些回应了这座城市春天的经历。唐潮的“话音未落”(Vanguard画廊)用数码建模将经典电影里的场景人物重构为一组由分镜头构成的“心之电影”,对应忧郁、愤怒及恐惧等私人情绪。钟云舒的“定福灶君”则将家里的各类厨房用品复制进Linseed空间的顶楼露台,开始发芽的蒜头测量着时间的流逝,隔壁邻居的厨房飘来阵阵菜香,而供灶神的神龛式空间则是艺术周里静下来冥想的好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