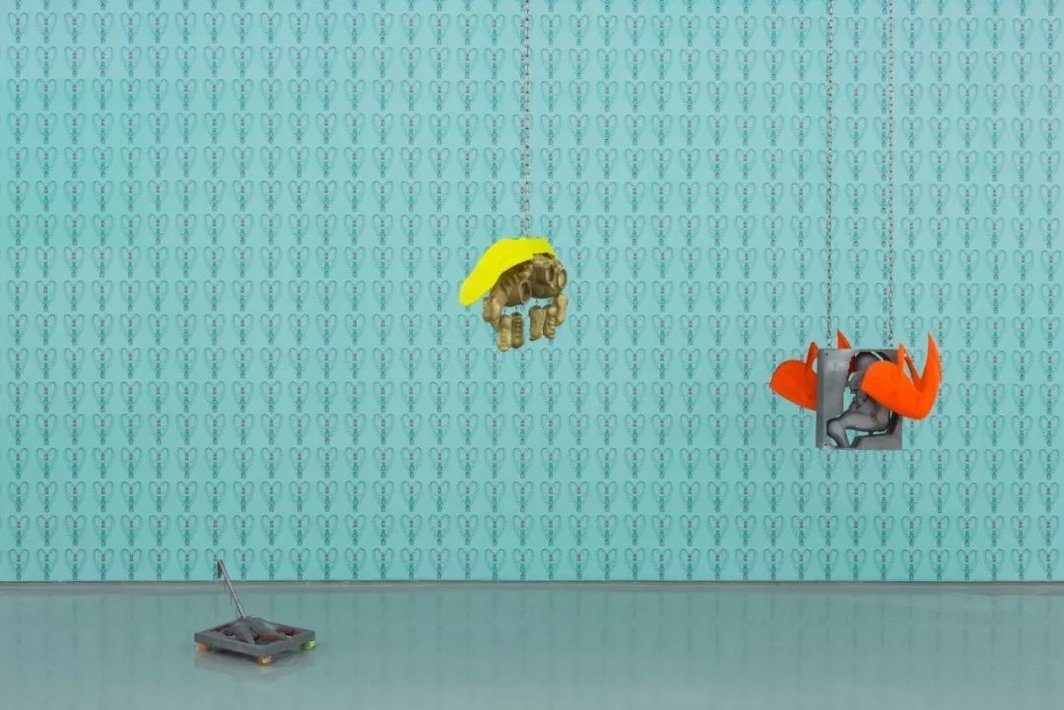李继忠
李继忠在黄边站的驻留总结展“郊外”现场出现了狭道、砖瓦、碎石及海洋的意象,此次展览是他“通向深海的狭道”系列的进一步延伸,处理的是日本在华细菌战以及由此造成的离散问题,其中尤其以曾经作为日军人体实验基地之一的广州南石头村难民营为叙事基点。此次李继忠以一个具体的行走路线串联起他的装置、行为和录像,赋予了所谓的“狭道”情感上的重量。除了我们熟悉的社会介入及田野调查式产出之外,李继忠还以行为艺术的方式重演了当年南石头难民营难民挖掘自己坟墓的悲剧性场面(《挖掘工》, 2019)。录像每个章的叙事都像是一个有序的维度碎片,补完他个人叙事中隐秘而复杂的细菌战研究逻辑。
在我的观察中,黄边站跟艺术家合作的方法很多,每次都会根据艺术家的性格、创作风格和生活节奏而调整,相对来说自由度很高。其实之前我提案是另一个项目,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被某种迫切性追回到“南石头”这个项目。黄边站能够提供的帮助则是从非官方的角度切入历史叙述。我一直都从事档案研究、介入档案文件系统,以及研究历史叙述透过怎样的方法呈现和输出。但在内地,通过官方途径介入档案有难度,那一套工作方法就失效了。所以档案不再只是关于内容,还是方法和沟通。
在田野方面,黄边站协助联络了两位本地学者谭元亨与沙东迅,以及南石头村的居民吴建华先生,之后又衍生出了数次的对话、行走、访问、户外放映活动。工作过程中我一直在反思“磨合”这件事。自从去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