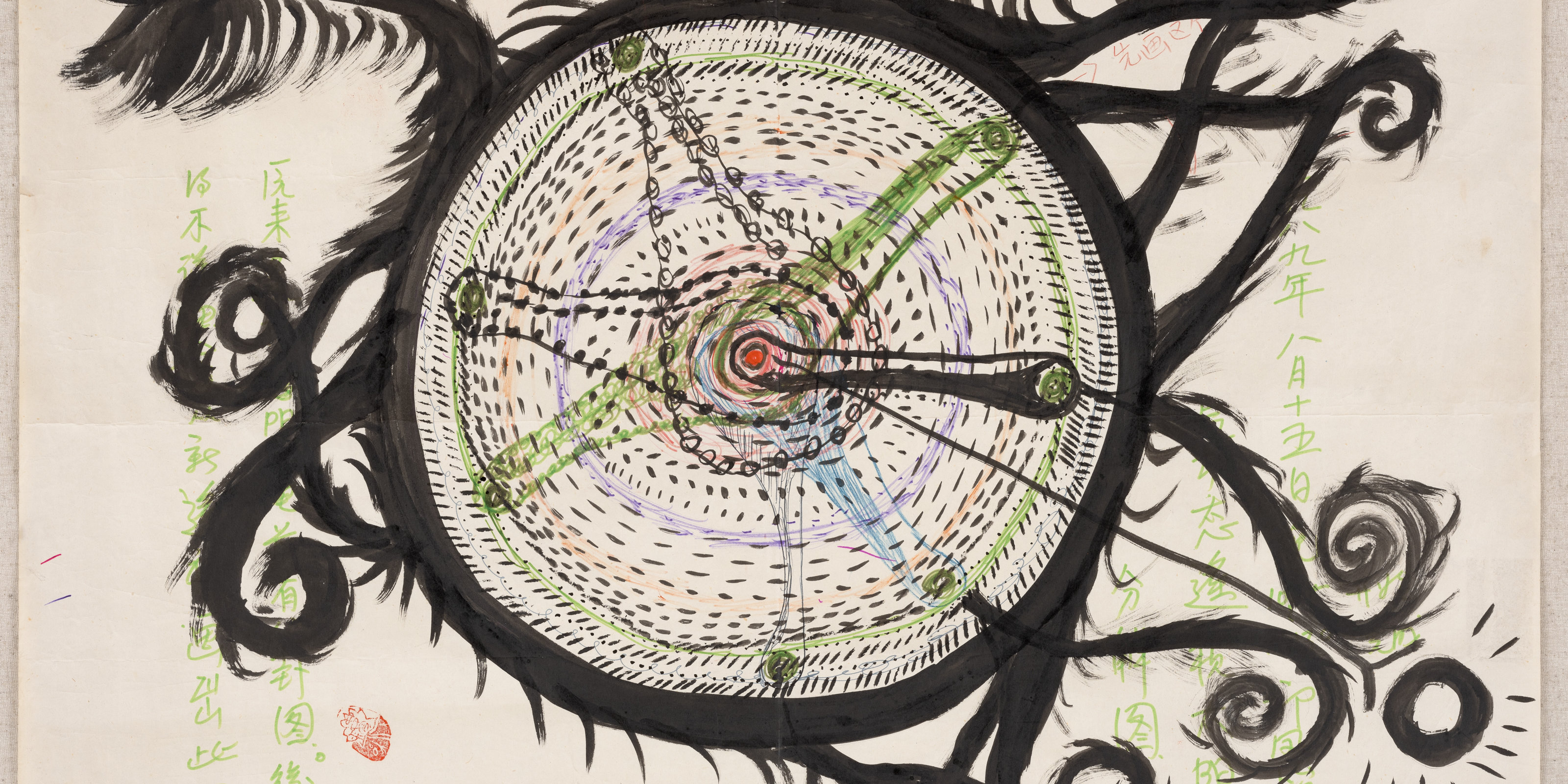第15届上海双年展
感知是政治吗?这也许是我在看过第15届上海双年展后留下的最大疑问。
时至今日,我们对于通过动物或植物视角来理解世界事实上并不陌生。各种生物都可以被作为理解世界、伦理、权力结构和人类感知边界的媒介。也许,这是将人从人类中心主义式的“自大”中解放出来的有效途径。本届上海双年展主策展人凯蒂·斯科特(Kitty Scott)的思路似乎正是如此:她引用“花瓣可以察觉蜜蜂翅膀震动频率继而改变花蜜浓度”这一科学发现,并从中建立一种跨物种式的理解路径,将对感知客体的注意力挪移到感知的主体之上。
几乎每一届上海双年展,都会在PSA一楼的偌大展厅里安放巨型装置以“填充”空间。或许是为了呼应本届主题中的花儿视角并建立初步印象,艺术家组合阿洛拉与卡萨迪利亚(Allora & Calzadilla)的作品《移植(森之幻影)》(Graft [Phantom Tree], 2025)宛如一大片明黄色花海,被悬挂在PSA的一楼大厅。如果代入双年展的语境,比起生态隐喻,我更关心那些无根亦无枝的形态——它们仿佛撤销了植物身份,这种被剥落的感觉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当下的艺术系统:在一种悬浮的状态与日渐架空的转译下,如何重建感知?
感知……的确,自启蒙运动以来,随着理性升位,感知便不断被低估。策展人显然意识到感性的缺席给当前艺术界带来的困扰,这几乎成为本届双年展的核心使命——重提感知,或者说再次重提“本就被低估”的感知。由此,我们看到一些作品之所以被“选中”,似乎正是因为其创作中散发的感性与松弛。弗朗西斯·埃利斯(Franc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