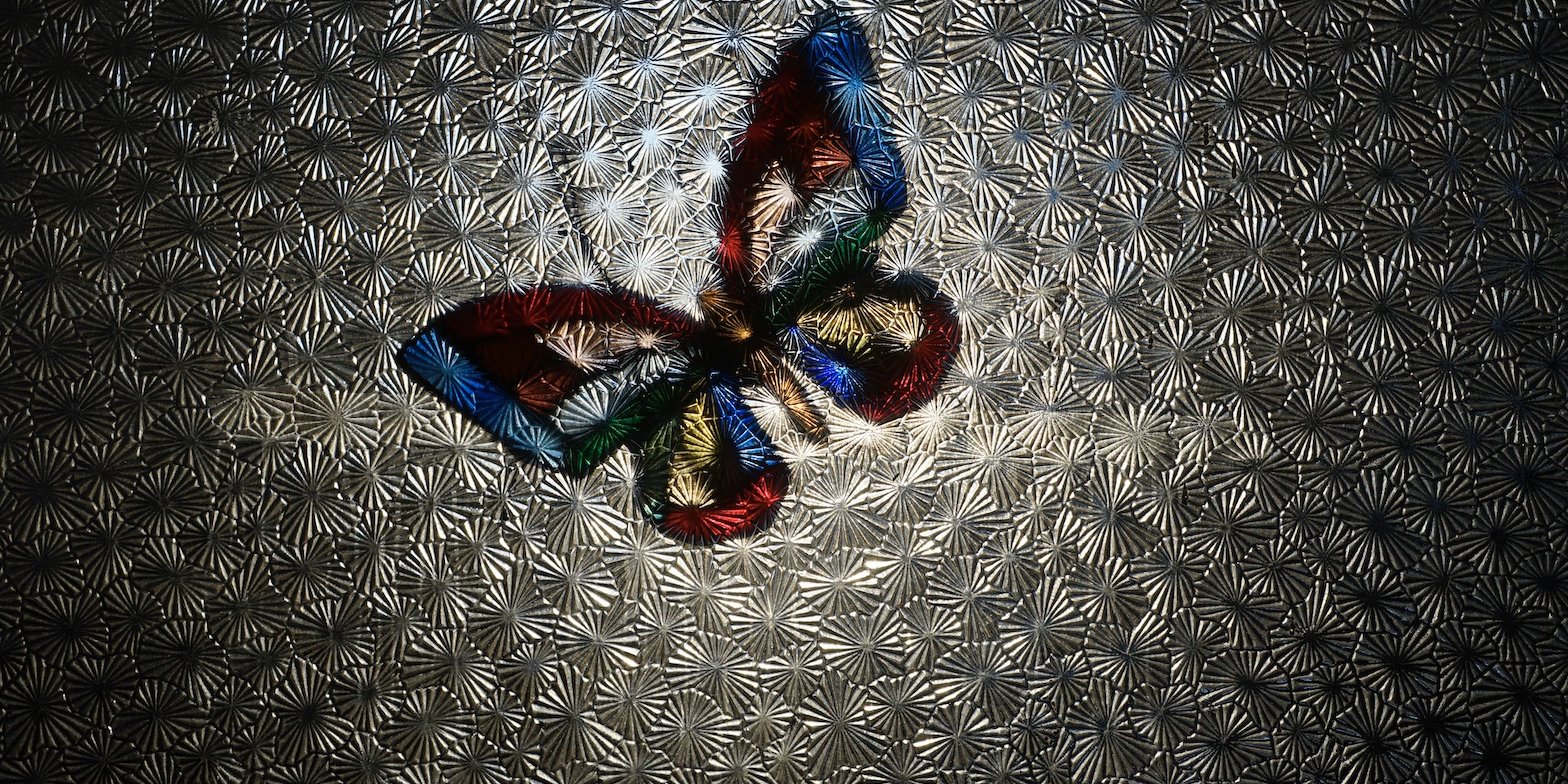“基础设施的地缘政治:当代视角”
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当代艺术博物馆(M HKA)举办的展览“基础设施的地缘政治:当代视角”(The Geopolitics of Infrastructur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通过来自世界多极的艺术实践,探讨基础设施与地缘政治、资本流动、殖民遗产和生态危机之间的交织关系。展览超越了对“基础设施”的技术性理解,将其作为进入当代世界权力结构、社会治理逻辑与知识建构方式的关键切口。展览在结构上也颇具野心,不仅在主题层面展开对全球化、殖民遗绪与地缘政治的讨论,也在形式语言上搭建了一个“流动的思考场”——一座融合研究、图像、声音、感知与情感共置的策展装置。
在日常经验中,基础设施往往是隐形的,只有在失效、崩溃或危机中才会显现。这种对“不可见政治”的关注,使本展不仅仅是在讨论技术网络,而是指向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论。它邀请我们重新训练视觉与判断力——看见那些不被看见的结构,理解它们如何深刻塑造人类的行动轨迹、资源分配与身体存在,并思考现行体制的替代可能。
展览中有多件作品并不以艺术家主观性为核心,而是通过协作与结构性的方式介入世界机制。米尔万·安丹(Mirwan Andan)与伊斯万托·哈托诺(Iswanto Hartono)回访印尼的GANEFO运动(Games of the New Emerg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