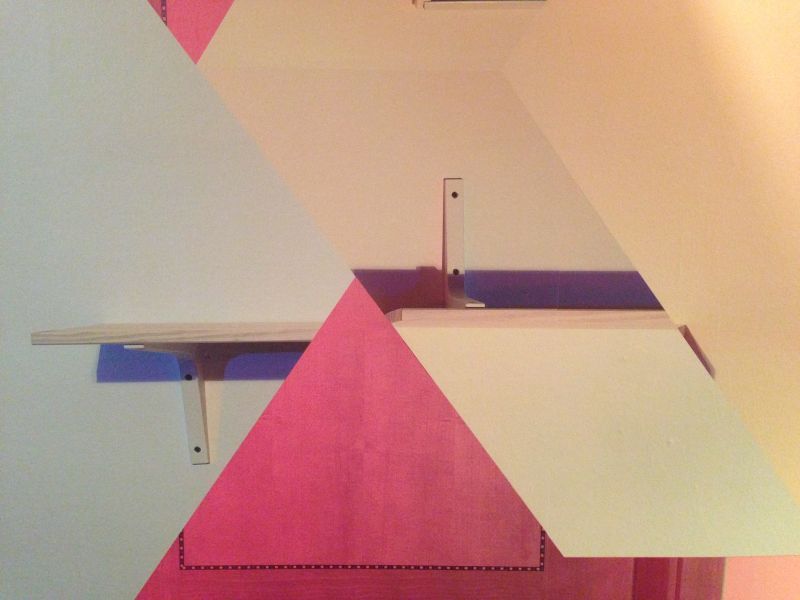陈轴
陈轴作品中反复出现的虚拟互联网世界,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存的另一个现实空间,它与人的回忆空间、抽象的情感空间共同构建了另一个“真实”世界,而这正是艺术家在近期电影创作中,通过不同“空间层”来描述的人群处境。本文中,陈轴详述了最近两年在创作上关注的问题,以及此次在香港白立方的个人项目“蓝洞”的呈现方式。项目展览将持续至8月25日。
我早期的录像作品主要关注人在日常空间中的重复性工作。我现在的创作依然在探讨这一问题,只不过重点转向了一群人在当下巨大的社会空间中的处境:这些个体被囚禁在一个巨大的空间里,难以突出重围。我仍然能感受到其中的荒唐,因为我觉得人是自由的,这也是我一直关心的核心问题。我以前影像作品的表达方式非常戏剧化,而现在更加生活化,戏剧的张力变成一种与观众的潜在沟通,而不仅仅是一种视觉上的张力。电影与纯粹的录像艺术的不同之处在于:电影有肉感,有情感和叙事;而录像艺术从大的范围来看,叙事和情感很少——录像艺术可以直接跳到非常抽象的层面去谈问题,但它不一定具备能在情感上让观众感同身受的叙事。对我而言,创作是一段旅程,我希望带领观者或我自己一点一点地从一个熟悉的风景离开,进入另一片陌生的风景。这是我最终想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对我的创作非常重要,它是未知,其中有自由和新。
《模仿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