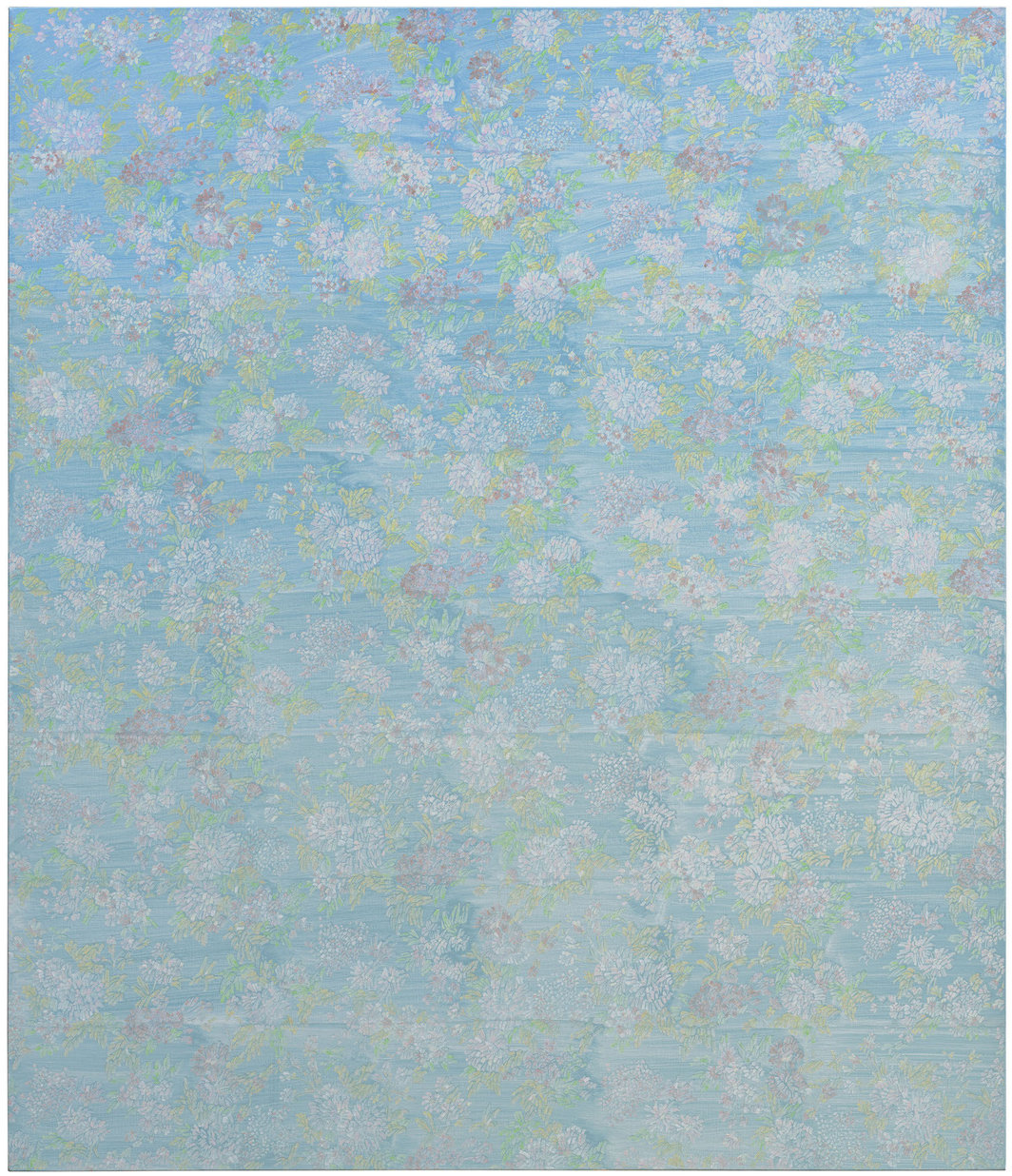错位的身体:在城市建筑与艺术的交汇处
新的空间实验浪潮正在当代艺术、建筑和日常经验的交汇处涌现,北京、上海、广州等“巨型城市”的艺术家将居住在都市飞地的心理和生活现实转化为艺术。虽然在装置艺术这一媒介中,空间处理似乎是意料之中,但中国巨型城市的各种条件促成了一条有趣的进化轨迹。本文将讨论近年发生在北京的三场展览和一个项目,建筑、空间、身体与空间的关系,以及既存的材料或条件在其中均被作为商品处理。此处的空间是从最宽泛的列斐伏尔意义上来理解的——从有机都市到基建空间[1],以及其中迥异的社会状况。而艺术家和艺术团体动用的方法包括建筑挪用或干涉,将建筑原材料转译为“艺术界”语境,或是与他们周边建造环境直接相关的创造性策略。同时他们共有的一个特征是,尽管使用大量熟悉的材料或场景,最后生成的都是一种去中心化和去方向化的现象学体验。
虽然对空间、建筑或社会语境的艺术性关注并非中国独有,但这里独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激励出创造性的策略。利用私人展览空间的灵活性和较为低廉的物料及人工费用,艺术家有机会创造出结构上雄心勃勃的情境,并由此编码出一种嵌入式社会批判的微妙形式。这些同时回应当地情境和全球话语的艺术家都不依赖于传统“中国性”符号,相反,他们选择符合其建筑和社会环境的传统材料,创作出抵制会被消费成“图像事件”或景观的艺术作品。[2]
紧密空间:语言与非
作为“装置艺术”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克莱尔·毕晓普(Cla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