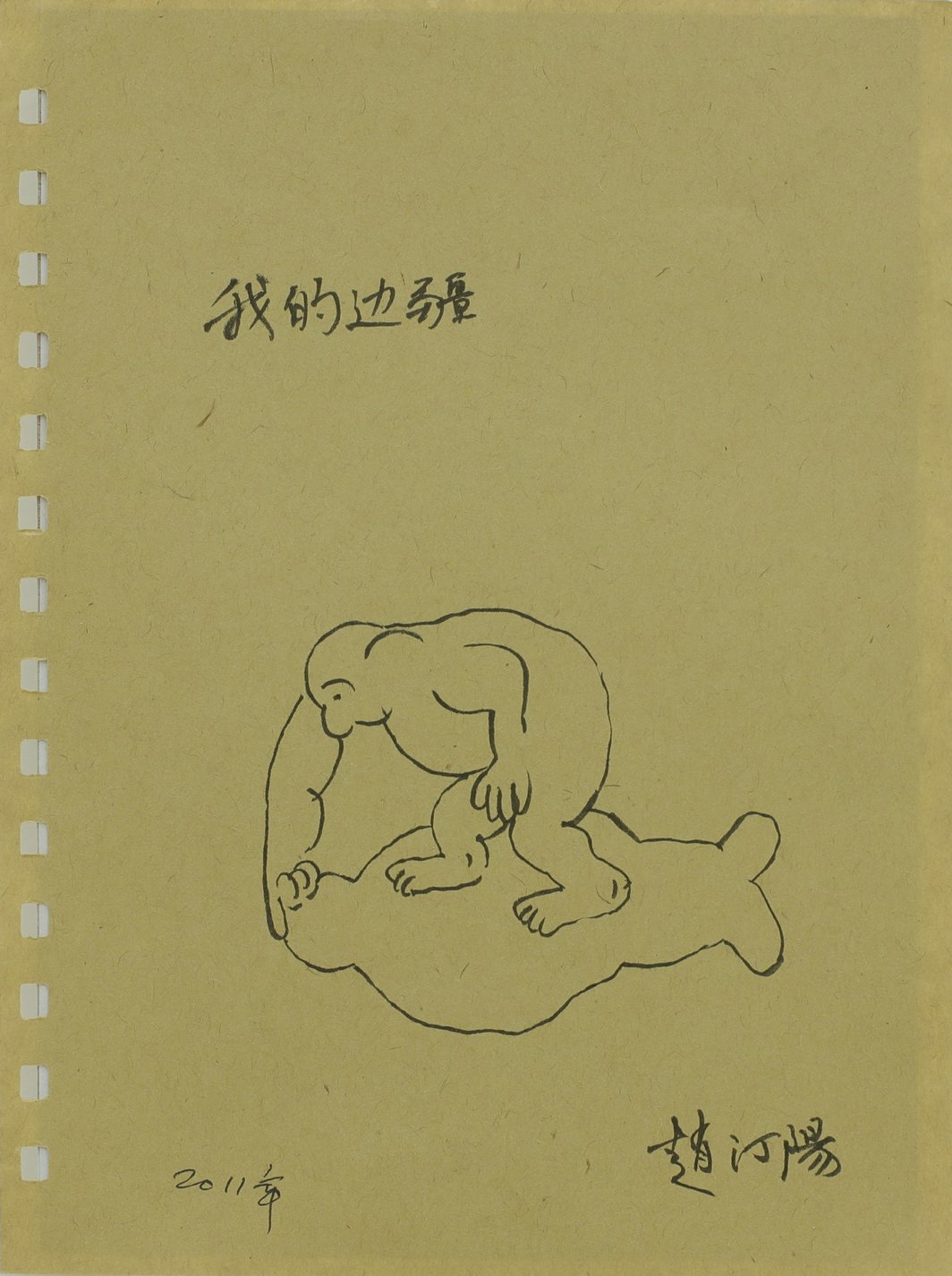珗宇
名为“茧房”的珗宇(Sun Woo)个展现场,若干炭化木板铺设的墙面穿插在白盒子空间中,如同现实世界强行介入的一个注脚,不仅打破了一般展陈的中性基调,也与展出的画作形成了一种戏剧化的张力——在炭化木板的反衬下,画作的实体边界被削弱的同时,图像的真实感反而被强化了。尤其是在面对《欢筵》(2025)这类大尺幅作品时,这种增强现实的布展手段,营造了一种剧场般的观看氛围。
珗宇的绘画虽然具有写实的特征,但呈现的却是一个由符号与象征物构建的异质空间。即便画面中没有出现任何人物形象,观众依旧能从长发、麻花辫、缝纫机、炊具、浣洗工具等物像组合中,辨识出家务劳动缠身的女性身份。考虑到珗宇是一位生活与工作在首尔的韩裔加拿大女性艺术家,这种图像组合便有了更为明确的文化指向。
在东亚文化语境中,女性话题仍常常与家庭角色绑定,而“贤妻良母”作为一类理想化模型,依然是一种总体性的社会身份枷锁。珗宇画作中具体的形象缺席,让某种“赞美”失去了对象,反倒暴露了那些用于塑造形象的“工具”本身。因此,我们在珗宇的画作中看到了阳光,却感受不到温暖。这种光线似乎与自然无关,而是一种工具理性的思想反光,折射出当代生命政治的冷酷。
或许,这也是珗宇选择写实绘画的原因——以具有数字渲染般质感的逼真再现,对应现代社会的系统逻辑。亦如英文展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