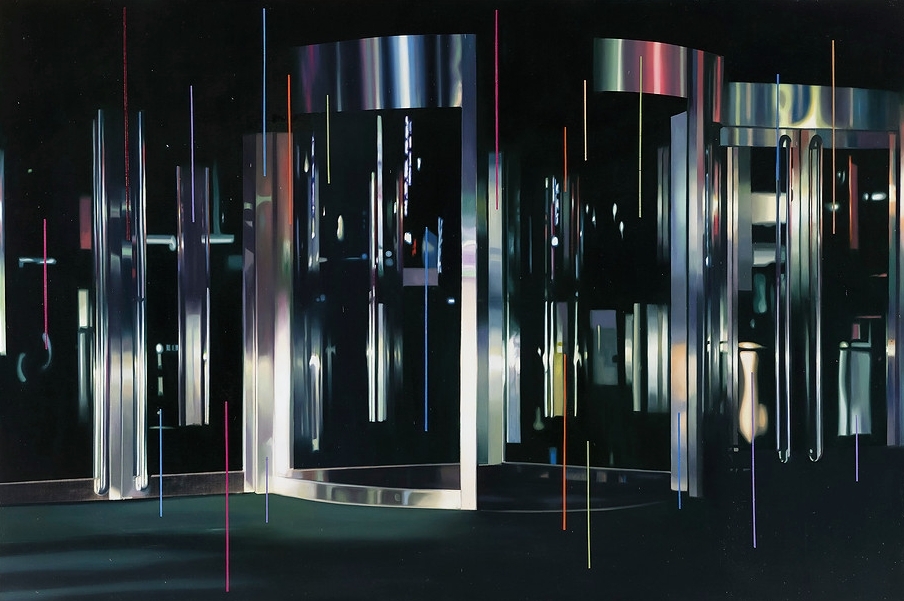佩恩恩
艺术家佩恩恩的最新个展“匹配池”正于OCAT上海馆展出。佩恩恩的创作也许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经济-艺术复合体”,其擅长以具有“挑衅性”的方式揭示某些真正起作用的“基层结构”,这些结构往往既是社会的,又是欲望的,既是技术的,又是身体的,既是合法的,又是非法的。在其最新实践中,艺术家讨论了“匹配”的暴力属性,类似于哲学家弗兰克·布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曾提出的金融的抽象暴力,“匹配”同样透过“竞争-合作”模型创造出一种残酷的社会动员与淘汰机制。在这篇访谈中,佩恩恩谈及了其创作的出发点与核心理念,并且为他所理解的艺术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说明。展览将持续至5月8日。
虽然我对于经济学感兴趣,但我不认同经济学意义上的分工,我也不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分工中开展我的工作。可以说,我对于经济的理解非常“另类”,我抽取的经济模型无关财富的增长,而是关于:每个人也许都可以从不相信以货币计量事物的价值开始,从而创造自己的经济学。虽然我的一些创作看似“恶搞”,但本质上是严肃的。比如在早期作品《每个人都是企业的同时也是产品》(2015)中,我扮演了一个投资失败的水怪,混进了传销团伙,揭穿了传销分子将公共艺术作品解释为财富神话的伎俩。对我而言,这就是一种“反经济”的经济学,让经济变成了某种带有自主性的、介入式的实践。
我也对非一般意义上的色情感兴趣——对我来说,当事物开始与其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