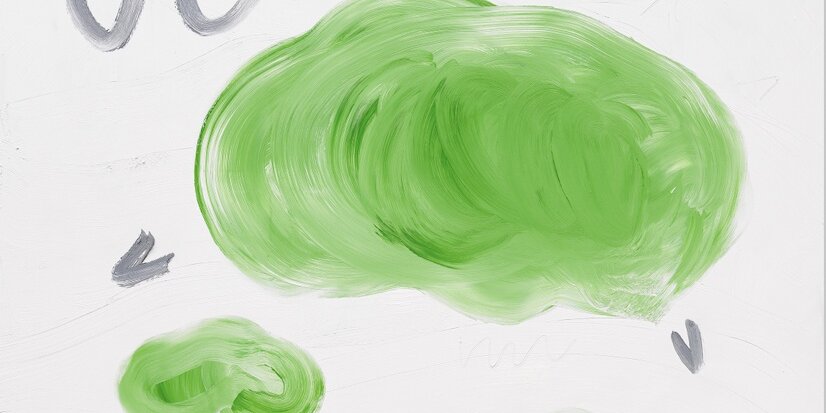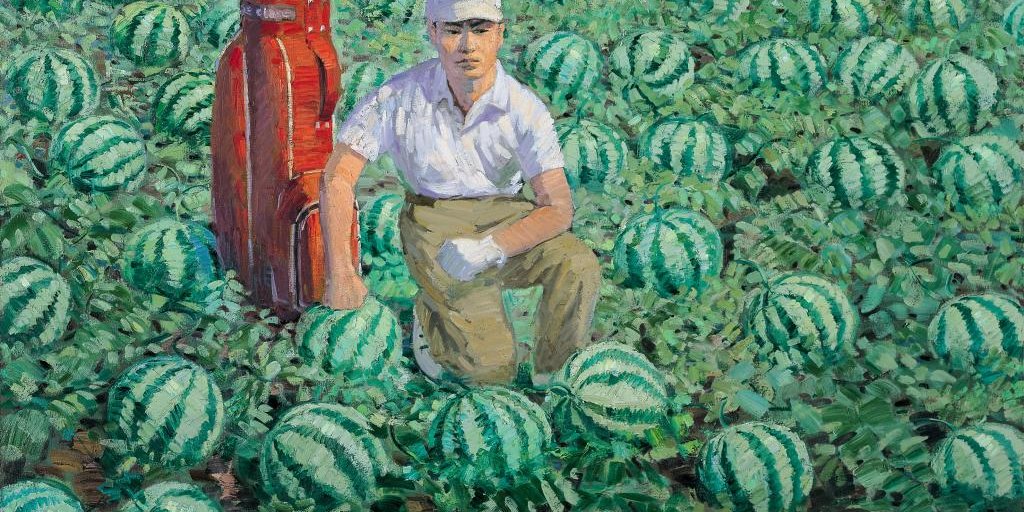“带电的孩子”
当21世纪耗尽四分之一时间,由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组织承办的第八届国际跨媒体艺术节以“带电的孩子”为主题,让人们再度关注电力时代的艺术。坦率说,这多少显得不合时宜,却又不可避免。它的必要性并不在于电力是影响我们生活的新兴技术或者前沿问题,恰恰相反,正是我们太过依赖这种“旧”技术,使得没有电力的生活不可想象,它才显得尤为重要。
尽管人类首次对电进行系统性研究可以追溯至17世纪初,到19世纪法拉第发明发电机,标志人类技术已可以自主掌握电力,但社会文化领域进入“电力时代”则要推迟到1960年代——彼时,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提出这一术语,用以描述电力作为媒介技术对社会形态的变革性影响。它消除了物理空间的距离,促成“地球村”;而电也成了人类的身体延伸,或者说技术“幻肢”。而真正形成全球趋势的艺术电力时代,大致是2010年代前后。依托全球各地双年展和艺博会的兴起,人们逐渐开始产生下述印象:一件没有电源开关的作品几乎很难被归类为当代艺术了。
据介绍,本届跨媒体艺术节主题“带电的孩子”得名于1988年上映的国产科幻电影《霹雳贝贝》——在剧中,少年贝贝拥有意念发电的神力,却也因此与周遭人群格格不入,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这种超能力。如今,这场集体记忆中的科幻往事已成每一个人的生活现实。“带电的孩子”也宣告着两层含义:我们的文化语境早已带电,无法摆脱;并且,在诸多技术的叠加影响下,我们仍旧只是电力文化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