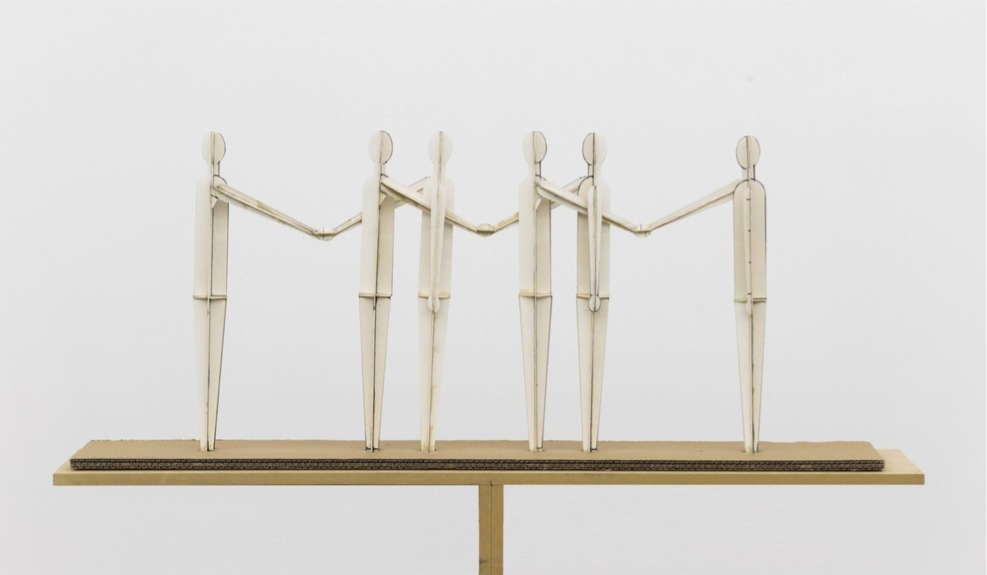何恩怀
在定居美国及工作的数十年后,何恩怀(Christopher K. Ho)从2016年起便不断重返他的出生地香港,他的一系列近期创作也多围绕自己作为华裔离散族群一分子的生存经验和感知展开。不过,从他在广州和香港两地的最新展览可以看出,艺术家尽量避免任何有过分显明的身份标记,作品的政治潜能毋宁说是体现在方法论中:通过对空间、计量标准、测绘仪器、建筑方法和准则等一系列具有“普遍效力”的概念或事物施以聪敏的反转,何恩怀用“以其之道还诸其身”的方式,将现代世界的权力话语延展至其逻辑的终点,剥出隐于其中的荒谬与残酷。
《水滴鱼》是我为广州时代美术馆展览“忘忧草:考古女性时间”完成的委任创作。经过和策展人的讨论,我决定利用展览入口的展厅再现一个曾被认为且仍在某种程度上被指定给女性专属的活动空间——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的内部环境。
现有的艺术史叙事将今天的艺术作品划分为“物”和 “整体装置”(total installation)的两极(图表1)。这套二分法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艺术-商品的关系而展开的,或者毋宁说,是对艺术商品化的一种持续抵抗。后者可以溯源到上世纪的的最初十年中杜尚关于现成品的大胆实验。到1990年代,这个一度富于激进性的的转向逐渐开始同不断升级换代的资本主义合流。体验取代了物,成为新的商品。在这一当代艺术的展示体系和话语结构中,一个属于家庭的内部空间似乎不太容易找到它对应的位置。上述现实情境是最初吸引我的地方,也构成了我想象和处理这样该空间的大背景。整个展览实际上围绕一个特定主体而展开:她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位妻子,更是一个照料者,她的一生几乎被各种各样义务所填满,直到退休后才开始享有一点点独立和自由。这恰好同我前段时间在香港艺术空间Tomorr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