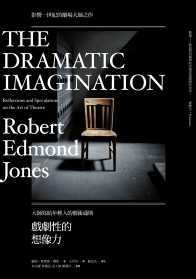蓝天碧水永处
《黄金时代》带给人的感受很复杂,绝不是痛哭流涕或抚掌大乐,更不是不痛不痒,或会心一笑;它甚至无法在今后的创作中充当任何教科书的角色,也不能提供什么激越的桥段。祖父苍老的脸,夸张的文明戏排练,年轻人踏过雪地的欢跃,从东北到上海,从重庆到香江,创作者为我们展开的那一幅幅白描的画卷。他们的手法不疾不徐,既不过分贴近权作代言,也不冷言冷语作壁上观,当事人徐徐道来,分寸拿捏得恰如其分,左联的作家并不都是我们以为的“左”,那些看似凄风苦雨的岁月也并不都是苦难更有温情脉脉,至于那一段段情感纠葛,更是不偏不倚,不过分描画,却是戏眼都在、精当无比。《黄金时代》的创作者们下手算得上“狠”。可是他们对剧中人宽容关照,却对自己狠得下心、下得去刀。这种宽严相济决定了本剧的气质奠定在种种“矛盾”之上却收获了平衡。
如果将本剧的文本放置在戏剧舞台上,那么《黄金时代》的样式算不上新颖。这种“新历史剧”与“文献剧”的做法其来有自,所达到的“间离效果”奠定了本剧的语法:打破观众在看故事的幻觉,拒绝情感的沉溺,引领观众思索。这种舞台感很强的剧本打法或许是因为编剧李樯出身于戏剧学院。然而,电影的镜头语汇则更有助于讲述者们更加自由的“跳进跳出”。从文本来看,这是一种既主观又客观的叙事,事件在不同讲述者的主观回忆中递进游走,忽而是旁观者,忽而是萧红本人;同一事件也会在不同当事人的口中进行陈述。正是这种多角度、极度主观的呈现导致本片相对客观的气质,创作者们试图从众说纷纭中与观众一起逐渐寻找、完善出一个萧红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