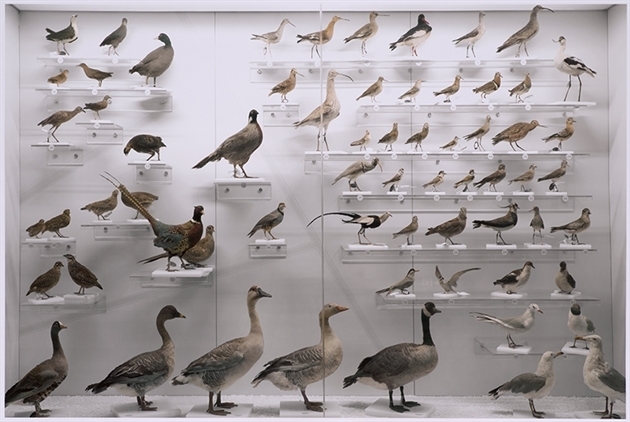谢南星
“香料”作为谢南星在国内首次美术馆级别的个展主题, 并没有为这七张容易令观者感觉费解的大型油画提供一个直观的切入点,而是巧妙地通过十五世纪末哥伦布在航海途中将树皮误认为印度“香料”这则充满隐喻色彩的轶事,为展览设定了认知纬度。虽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过程中的种种误读,甚至海上贸易可以把“香料”这一主题升华到文化真实性(cultural authenticity) 的问题层面,但对于一直以油画为主要创作媒介的谢南星来说,该主题恰如其分地将这一“非本土”的媒介推至前台。展览也因此成为一个契机,揭示了油画被引进中国后,经由印刷品等二手媒介传播,或是由于文化背景差异,其历史经典作品遭遇的种种误读,同时凸显了该媒介本身在现当代对于那些试图驾驭它的艺术家们提出的挑战。
可能只有艺术史知识渊博的观众才能像东门杨的语音导览那样,结合每件作品所对应的古典绘画色调及其历史语境,同时考虑谢南星所生存的环境,以及他作为中国艺术家所关心的问题,从细节到整体、全方位地解读“香料”。这样的观众固然对任何艺术创作来说都可遇不可求。不过,即便是普通观众,也同样可以通过观看,通过分解画面所呈现的信息来打开艺术家对于绘画的态度,或者说他作为一名中国画家与古典绘画的关系。从《香料No.2》(2016) 的暴力构图,到《香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