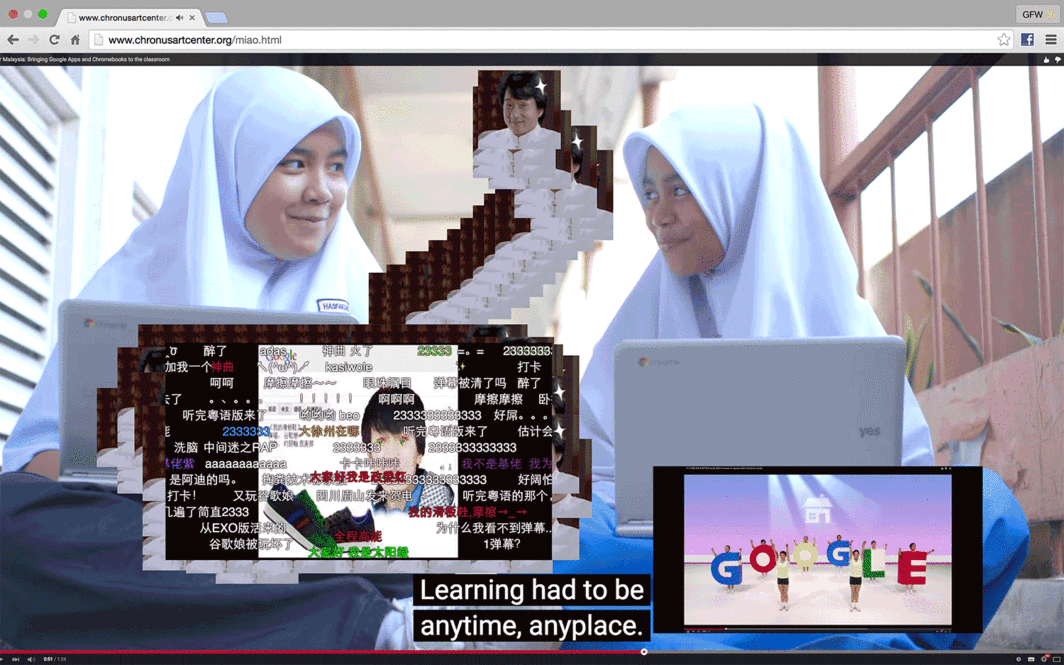见者的书信
如果我们追溯当代艺术近年来最显著的两个趋势——社会转向和媒体转向,有两位创作者的名字很难不被提及。在“见者的书信:约瑟夫·博伊斯 x 白南准”中,这两位同时代人既不乏呼应,又各自铺展出一片异质的领域,将艺术的概念与边界拓宽。
展览分为三个部分:一层白南准展区、二层博伊斯展区,以及位于一层中间以半文献半作品的方式突出两人交集的板块。对白南准的展示从年代和作品形态来说都比较全面,“录像之父”或者“第一位全球艺术家”这些称号相对于他对材料那轻松活泼但不乏张力的调用来说太严肃了。约翰·凯奇、金鱼、汉字、提琴、古董家具、鲜花、摩托、当时最新型的索尼或三星电器,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部分共同预测着一个不可逆加速媒介化的世界。
二楼博伊斯展区的重点在前厅的五只玻璃柜,其中装有他行为作品的“道具”或“痕迹”、私人物品、诸如玫瑰等作品中经典的符号物件、演示艺术家理论的图表等等。不同的玻璃柜中物件及其摆设是经过艺术家精心“策划”的,这样它们的收藏者拥有的便不仅仅是物体形式的艺术品。除此之外,其他展品多为生前的照片资料、展览卡片及海报,以及其他印刷品等衍生物件,如一张只印着一行字“艺术是当人们还笑着”、盖以博伊斯创办的自由国际大学之印章,再加上艺术家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另有两部黑白的行为录像,其中包括著名的《如何向死兔子讲解绘画》(1965)。博伊斯诸多巨型装置、他对通过艺术创造一个环境整体的尝试,甚至延伸出展厅的“社会雕塑”等就只能通过想象获得。博伊斯的创作体系庞杂而晦涩,展厅中一堆为了呼应作品而供观众拿尝的大白兔奶糖透露出策展方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