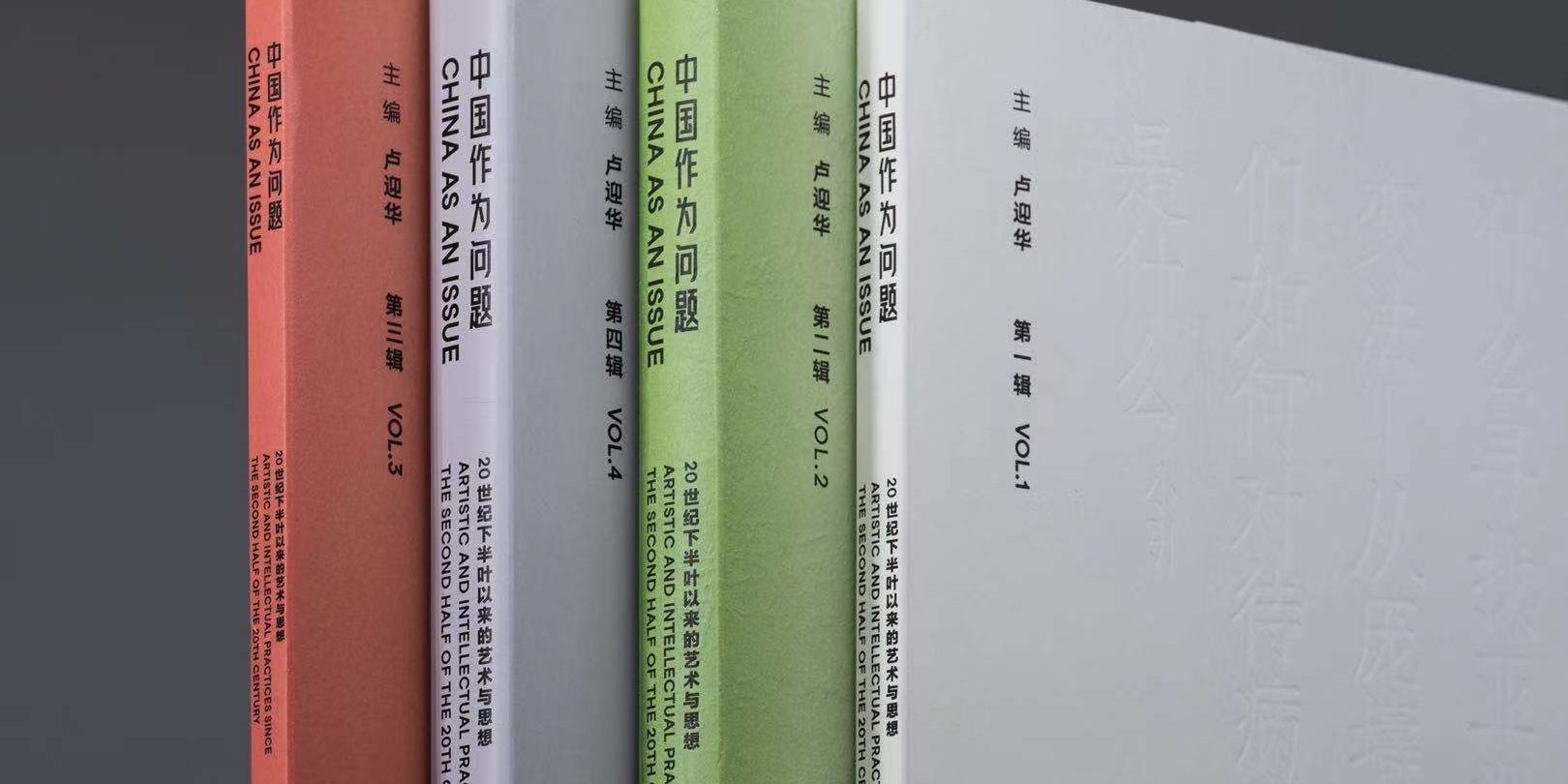通往能登之路
从上空俯瞰,金泽21世纪美术馆宛如一个平整嵌入城市的巨大的圆。圆周由全透明的弧形玻璃幕墙构成,消解了内外边界。图书馆、市民画廊、儿童工作室、讲堂等免费的公共功能区沿圆周排布,靠近圆心的部分则是付费展区,若干高地错落的方圆展厅如积木般散落其间,由纵横交错的通廊串联。新千年伊始,为妹岛和世与西泽立卫(SANAA)赢得2004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金狮奖的这座公共美术馆建筑,其所代表的灵活、开放、去中心化的空间理想,如今听起来几乎让人怀旧。21世纪刚过去二十多年,世界似乎正在滑向流动和透明的反面,危机——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生态的——已成常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SIDE CORE(目前由高须咲惠、松下彻、西广太志、播本和宜四名成员组成)是一个诞生于危机的艺术小组。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对都市社会带来的震荡为该小组的成立提供了直接动因。“艺术家在都市空间的生存之道”这一母题,贯穿了他们自2012年创立以来的所有实践,即便后来小组经常离开他们居住的大都会东京,到日本各地方调研参展。此次他们在金泽21世纪美术馆的展览“活着的道路,生活的场所”(living road, liv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