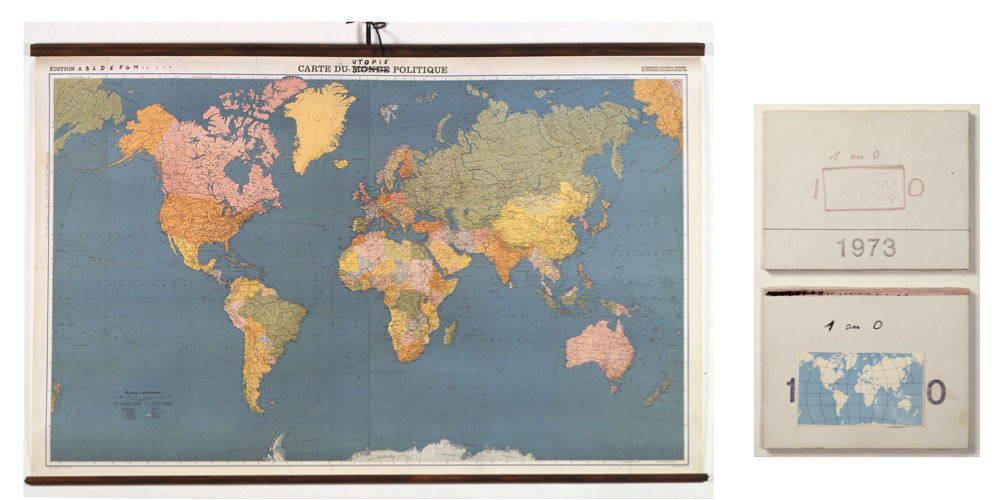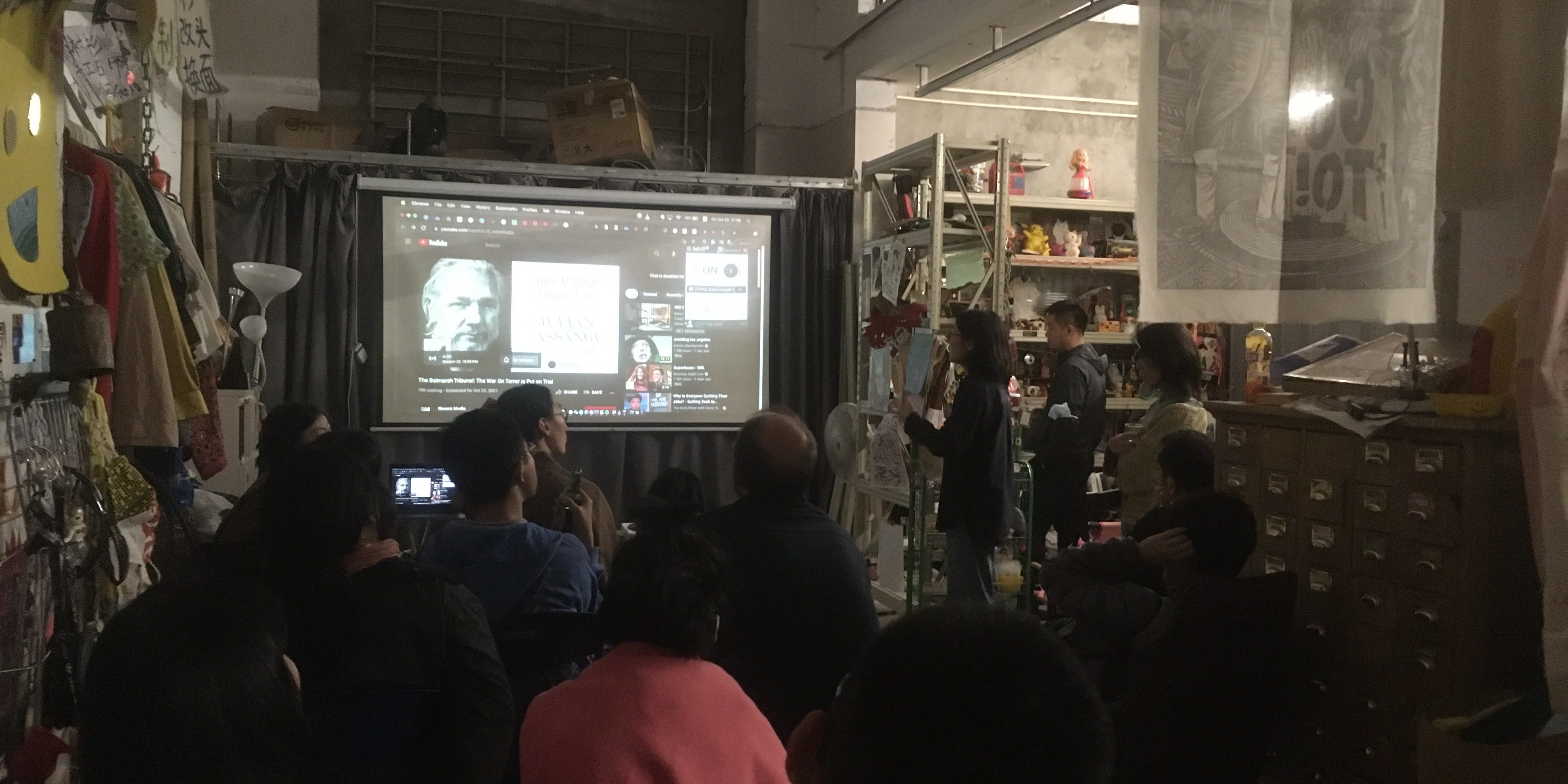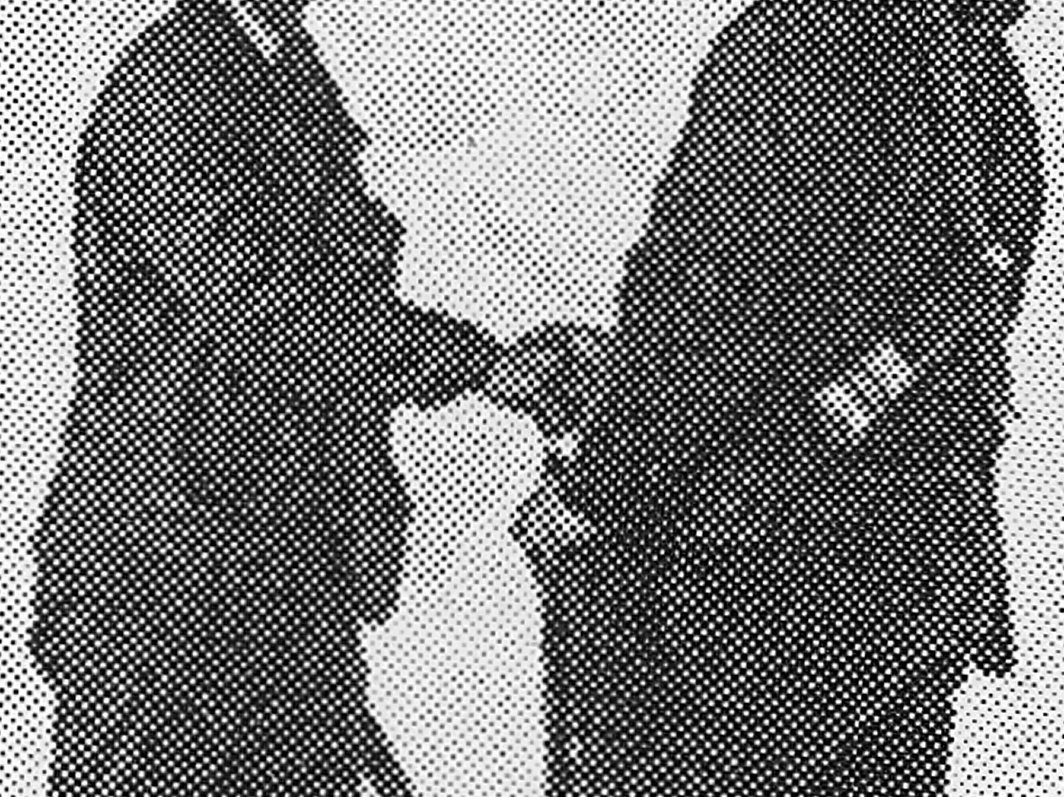体育课
“无政府够了没?马上回到团体队形!”一名舞者对另一名舞者喊道。出自芭芭拉·瓦格纳&班杰明·德·布尔卡(Bárbara Wagner&Benjamin de Burca)的作品《Swinguerra》(2019)中的这句指令也呼应了新北市美术馆展览“体育课”中的一对核心矛盾: 体育/运动作为一种载体,一方面体现了个体的解放和突破,另一方面又与国族身份、权力结构紧密绑定。如同我们在展览的档案陈列中看到的,板球之于印度,或是棒球之于台湾,前殖民地盛行的运动透露出殖民历史的规训效果,而新的身份认同又需通过体育竞技上的成功来加以巩固——奥运会无疑是最佳的表现场地,奖牌可以是霸权也可以成为打破霸权的象征。
以体育/运动为镜,人的身份与身体的关系既可以保守如藤吉维·尼基·恩科西(Thenjiwe Niki Nkosi)作品《同轨》(The Same Track,2022)里闪现的“大英国协运动会”(Commonwealth Games)上那些必然坚毅的面孔和必然强健的体魄(令人不得不联想到《意志的胜利》),也可以像阿莫·帕特尔(Amol K.Patil)的《溜冰鞋上的黑色面具》(Black Masks on Roller-Stake,2022)里改造过的自带清扫路面功能的溜冰鞋以及印地语音乐一样与阶级隔离、劳工抗争相关联。虽然二者都与集体-个体的动态关系密不可分,但展览中的一些时刻让我们想要更为慎重地区分“体育”与“运动”。作为激进左翼和女性,意大利裔巴西建筑师丽娜·波·巴蒂(L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