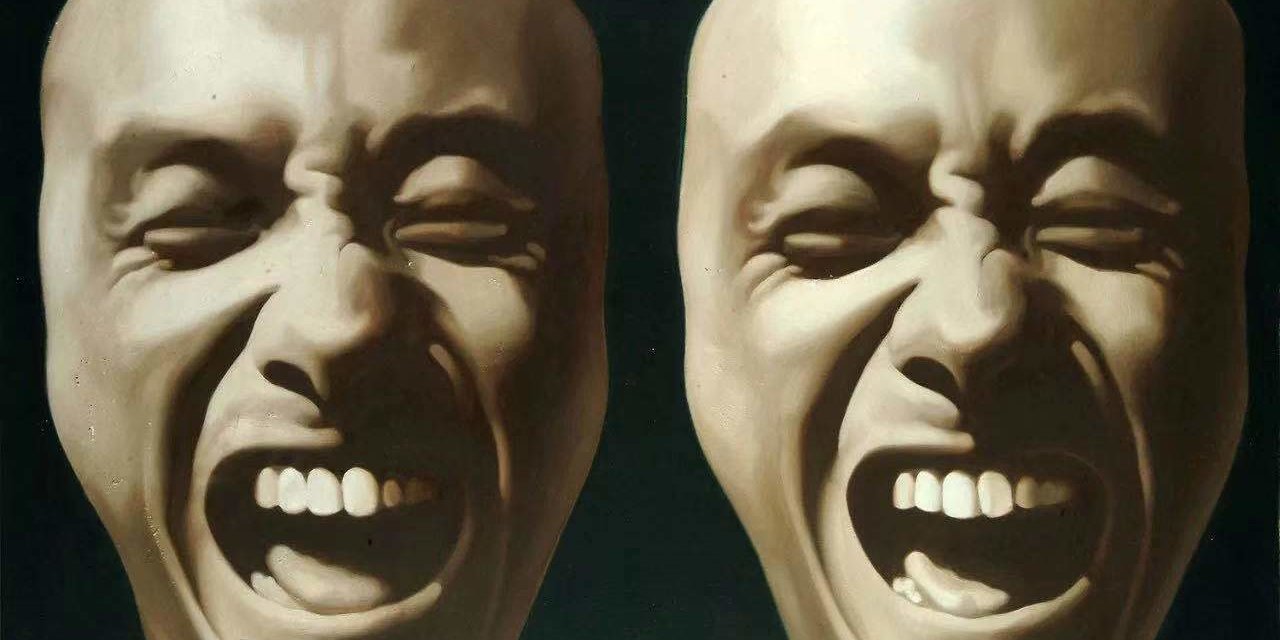黄安澜
黄安澜的最新个展“成为所有地方的所有人”观看起来并不轻松。我常在观影间歇停留,在影像和文字所勾勒的心理图景里适应不同代际的我们之间存在的“时差”,去识别我们共处的这个世界里个体可能都曾遭遇过的那些惶惶然的时刻,并对流散在这个时间差里难以被把握的部分投以更多关注。
在现场,观众最易注意到的是在明亮区域播放的新作《供认》(2025),碧水潺潺的画面记录了艺术家在北马其顿的一次湖上之旅。同船的还有阿尔巴尼亚船夫,塔吉克游客。整部影像里出现的只是映现着绿叶的水波,夹杂着船上人的闲谈,间或是没有参与交谈的艺术家在旅程结束后写下的文字。这些互不相干的话语伴随着荡漾的湖水,传递出一种闲散又略带忧伤的平静。作为背景的巴尔干半岛难免令人产生诸多联想,并为之赋予更多层寓意,但这些尚未进入谈话,《供认》就戛然而止。
同侧的墙上,一个锈迹斑斑的金属捕兔夹压在古董相框内平铺的白色旧手帕上,旁边稀散着一些散发光泽的小吊坠(《猎物》,2025)。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物件——爱荷华捕兔夹,北马其顿手帕,淘宝网购配饰——被禁锢在同一个框内,产生视觉的张力激发着观众对物品本身的好奇。如果不被提示,极少有人会取下相框看到背面的文字并探究其含义。据艺术家透露,这些印染在相框后的句子来自《供认》里船夫忽然哼唱的歌谣:“同志啊你别把轮胎弄坏”。这番匪夷所思又带有年代印记的歌词,被遮盖在夹缝层里。《猎物》的存在似是对《供认》的视觉注解:那些被期待说出来却又难以表述的,以另一种方式在流转。而不干涉的旁观,也可以成为一种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