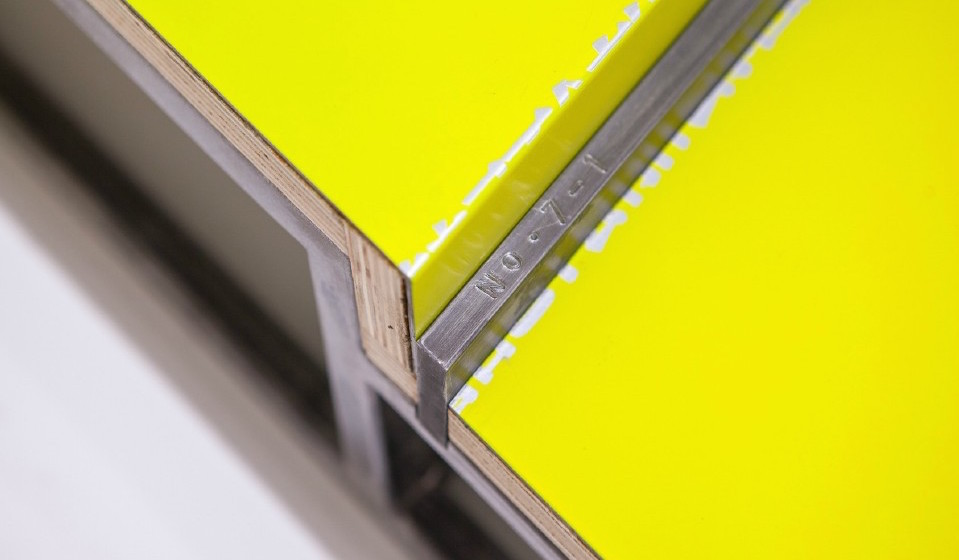梁硕
梁硕在此次展出的最新系列画作中完成了民间画法和传统山水程式的美学并置。与事无巨细客观描摹对象的十七世纪荷兰风俗画不同,中国传统山水画讲究心境与景观的合一,画面常用多点透视或散点透视,没有一个固定的观测点。摸山人移步换景观察山势地貌,回到画室再将身体性的空间认知摹写转移。梁硕画作中超现实的空间并置,正是基于传统山水画里多点透视的构建方法。例如,《夯土剧院》(2024)将这种结构塑造发挥到了极致:山土、石料、房屋如噩梦一般被地形串联在一起;山景和楼宇被冷暖用色分隔两侧,也分隔了渺无人烟的山林和人类聚居的都市。民间绘画在手法上体现为粗狂饱满的造型,浓郁奔放的用色;而题材上,常常就地取材于日常生活。作品《垰园》(2024)就将日常意象与传统文人画里常见的孤寂感纳入同一画面:废弃多年的旧工厂厂房中,鸟兽携带落下的植物种子生根发芽,长成大树。人类离去后的厂房重新被自然召回,焕发出平静的末世气息。
不过,展览题目(也是艺术家在这批系列新作中所用的化名)“梁大芬”在提示梁硕对民间绘画(以深圳大芬油画村为代表)的倚重的同时,也容易遮蔽艺术家的另一条思考路径,那就是他对画外山水对象的凝视,亦即画家将地质性的物理山水置入社会生活语境时对其进行的思考和转化。梁硕试图参照自己在无数次爬山过程中获得的肉身经验,借民间绘画的语法,反映当下物质性的山野现实状况。其背后的逻辑是,借助建造新的物质生态形式,也许可以进化出新的审美。这让人联想到上个世纪中期的“新国画运动”。配合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新”的山水画中开始出现水库、大桥、高压线等现代工业基础设施的图样。它们在客观事实上建构了一个新的系统,该系统彻底告别了传统的山水画尤其是文人画的审美趣味,在中国画的改良实践道路上创造出了新的式样。